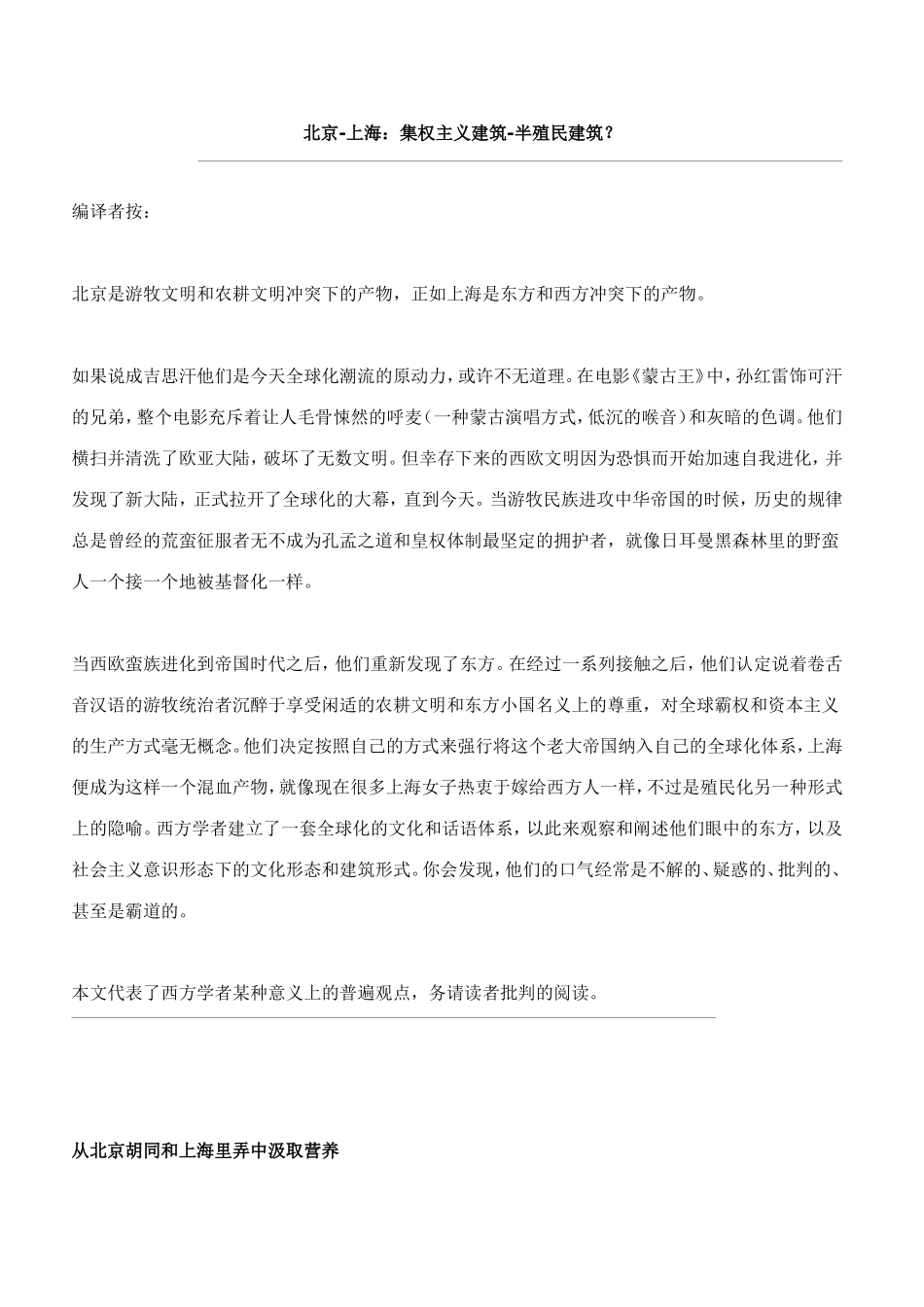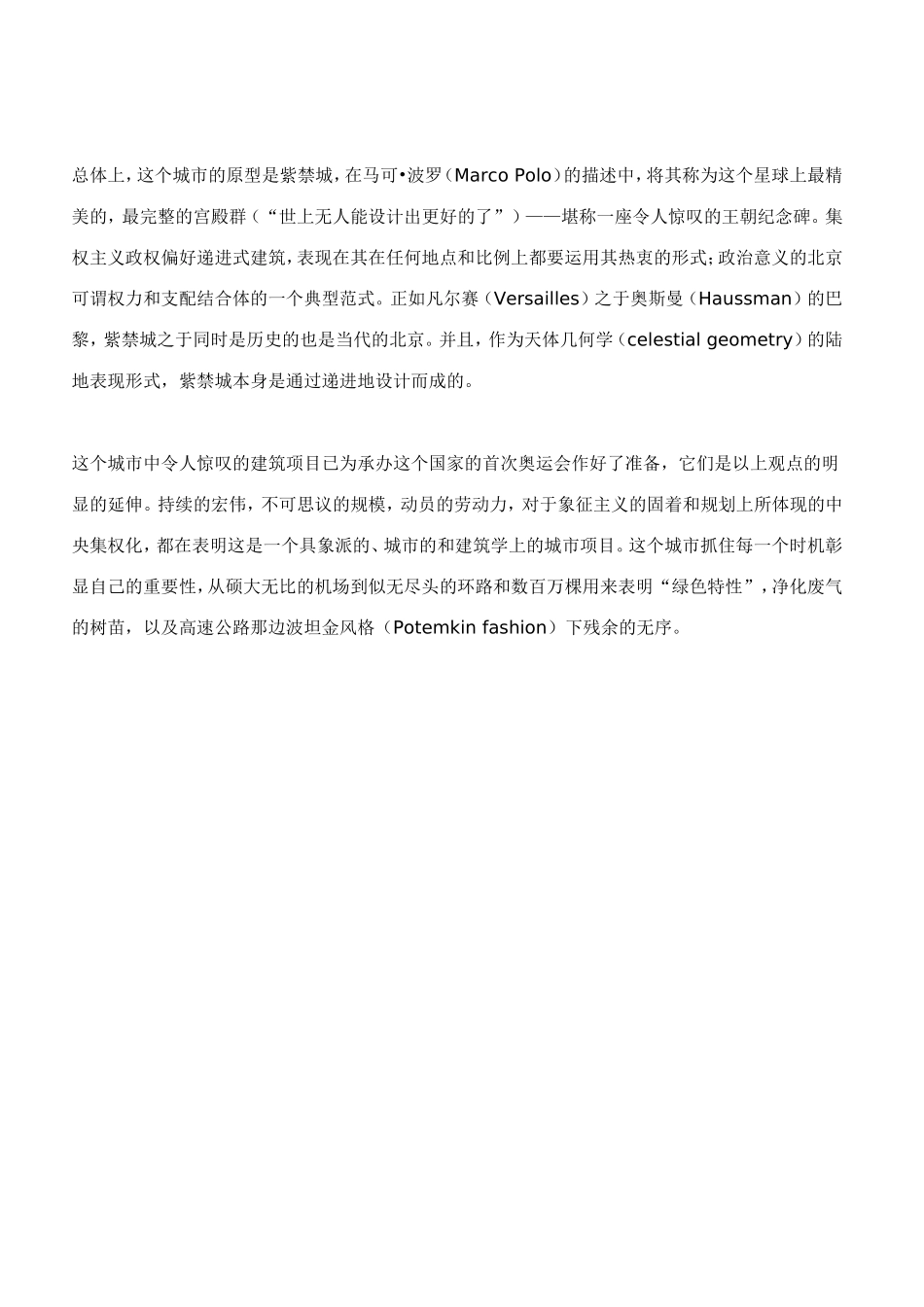北京-上海:集权主义建筑-半殖民建筑?编译者按:北京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冲突下的产物,正如上海是东方和西方冲突下的产物。如果说成吉思汗他们是今天全球化潮流的原动力,或许不无道理。在电影《蒙古王》中,孙红雷饰可汗的兄弟,整个电影充斥着让人毛骨悚然的呼麦(一种蒙古演唱方式,低沉的喉音)和灰暗的色调。他们横扫并清洗了欧亚大陆,破坏了无数文明。但幸存下来的西欧文明因为恐惧而开始加速自我进化,并发现了新大陆,正式拉开了全球化的大幕,直到今天。当游牧民族进攻中华帝国的时候,历史的规律总是曾经的荒蛮征服者无不成为孔孟之道和皇权体制最坚定的拥护者,就像日耳曼黑森林里的野蛮人一个接一个地被基督化一样。当西欧蛮族进化到帝国时代之后,他们重新发现了东方。在经过一系列接触之后,他们认定说着卷舌音汉语的游牧统治者沉醉于享受闲适的农耕文明和东方小国名义上的尊重,对全球霸权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毫无概念。他们决定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强行将这个老大帝国纳入自己的全球化体系,上海便成为这样一个混血产物,就像现在很多上海女子热衷于嫁给西方人一样,不过是殖民化另一种形式上的隐喻。西方学者建立了一套全球化的文化和话语体系,以此来观察和阐述他们眼中的东方,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文化形态和建筑形式。你会发现,他们的口气经常是不解的、疑惑的、批判的、甚至是霸道的。本文代表了西方学者某种意义上的普遍观点,务请读者批判的阅读。从北京胡同和上海里弄中汲取营养迈克尔•索金(MichaelSorkin)“我就喜欢大的。”——毛泽东,1958(不知道原话是什么)我经常到中国,但是不知何故,直到几个月之前才有幸到北京一游。北京和中国的大多数城市一样,不仅规模大得让人感到压抑,而且规划存在“自生自长”的风格。不过,和其他城市不同的是,北京拥有一个矩形的纪念碑(人民英雄纪念碑?),宽阔的林荫大道,间隔很开的建筑群以及厚重的帝都气质。总体上,这个城市的原型是紫禁城,在马可•波罗(MarcoPolo)的描述中,将其称为这个星球上最精美的,最完整的宫殿群(“世上无人能设计出更好的了”)——堪称一座令人惊叹的王朝纪念碑。集权主义政权偏好递进式建筑,表现在其在任何地点和比例上都要运用其热衷的形式;政治意义的北京可谓权力和支配结合体的一个典型范式。正如凡尔赛(Versailles)之于奥斯曼(Haussman)的巴黎,紫禁城之于同时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北京。并且,作为天体几何学(celestialgeometry)的陆地表现形式,紫禁城本身是通过递进地设计而成的。这个城市中令人惊叹的建筑项目已为承办这个国家的首次奥运会作好了准备,它们是以上观点的明显的延伸。持续的宏伟,不可思议的规模,动员的劳动力,对于象征主义的固着和规划上所体现的中央集权化,都在表明这是一个具象派的、城市的和建筑学上的城市项目。这个城市抓住每一个时机彰显自己的重要性,从硕大无比的机场到似无尽头的环路和数百万棵用来表明“绿色特性”,净化废气的树苗,以及高速公路那边波坦金风格(Potemkinfashion)下残余的无序。如此多的“雷”人建筑由外国建筑师完成本身也具有强有力的象征意义。数千年来,中国一直以排斥外来的非华夏的夷狄(non-Hanbarbarism)影响。特别是这个国家的近现代史被定义是与殖民主义、侵略、和帝国主义势力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这些意识形态包括所谓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事实上,当中国选择那条特别的道路的时候,其热衷建造的基础设施所反映的正是“我们”在上世纪50和60年代资本主义消费高潮时期的建筑和观念特点。汽车和其暗示意义被狂热地接受,制造出巨大的交通堵塞,高速公路扩张,污染以及其所有衍生物的蔓延。这种无节制的城市主义的杂交与全球化发展高度一致,并且和其他地方一样的是,拼凑下诞生的建筑形式交替地具备了畸形、迷人、让人生畏和熟悉的气质。对于一个陷于一种内部对与“对外开放”的争论之中文化来说,传统和全球化之间的冲突非常重要。这场争论一个具有启示性意义的事件就是去年故宫中从2000年就开始经营的星巴克被迫关闭。咖啡店的关闭是一些人请愿的结果——他们收集了50万个抗议“侮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