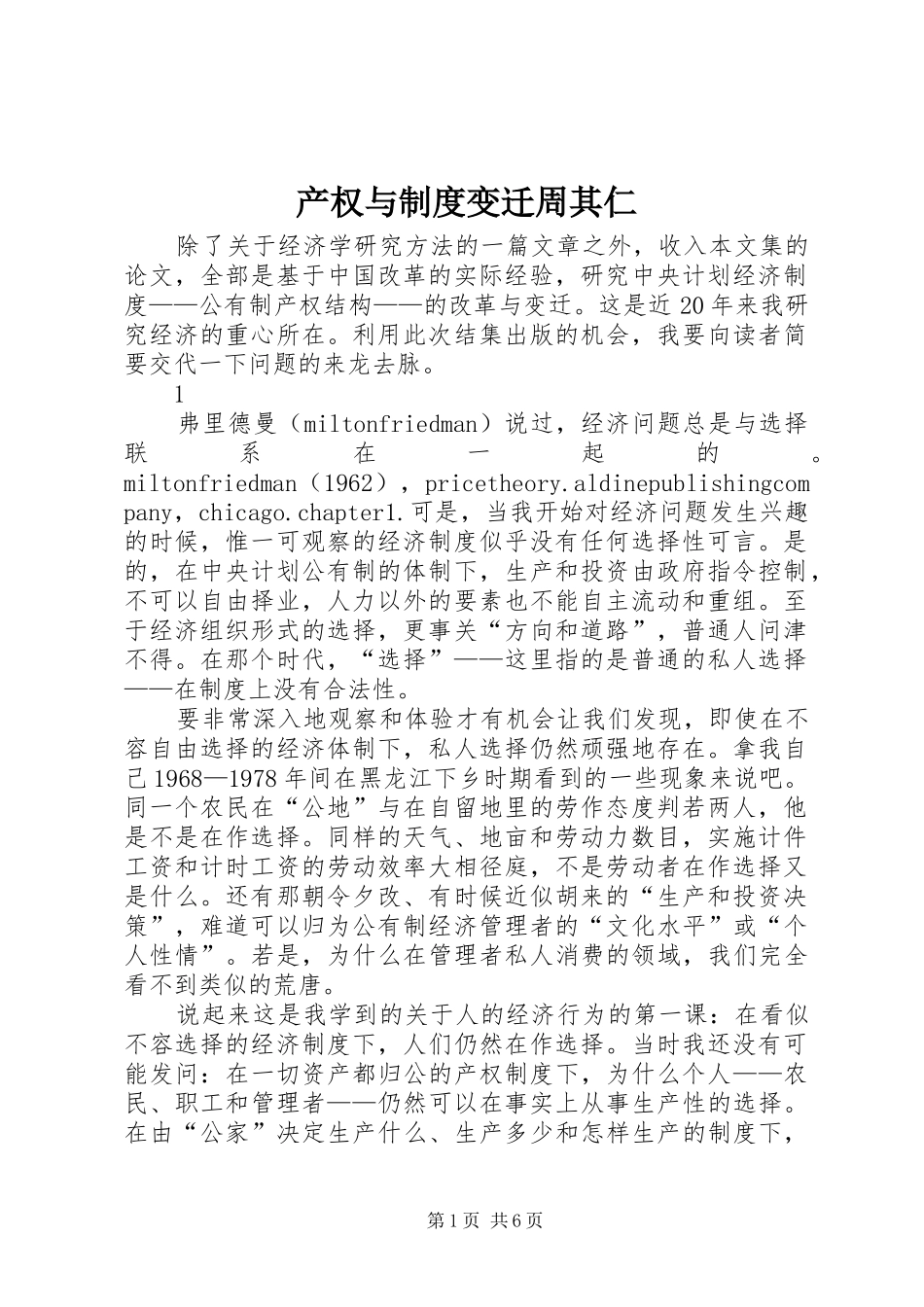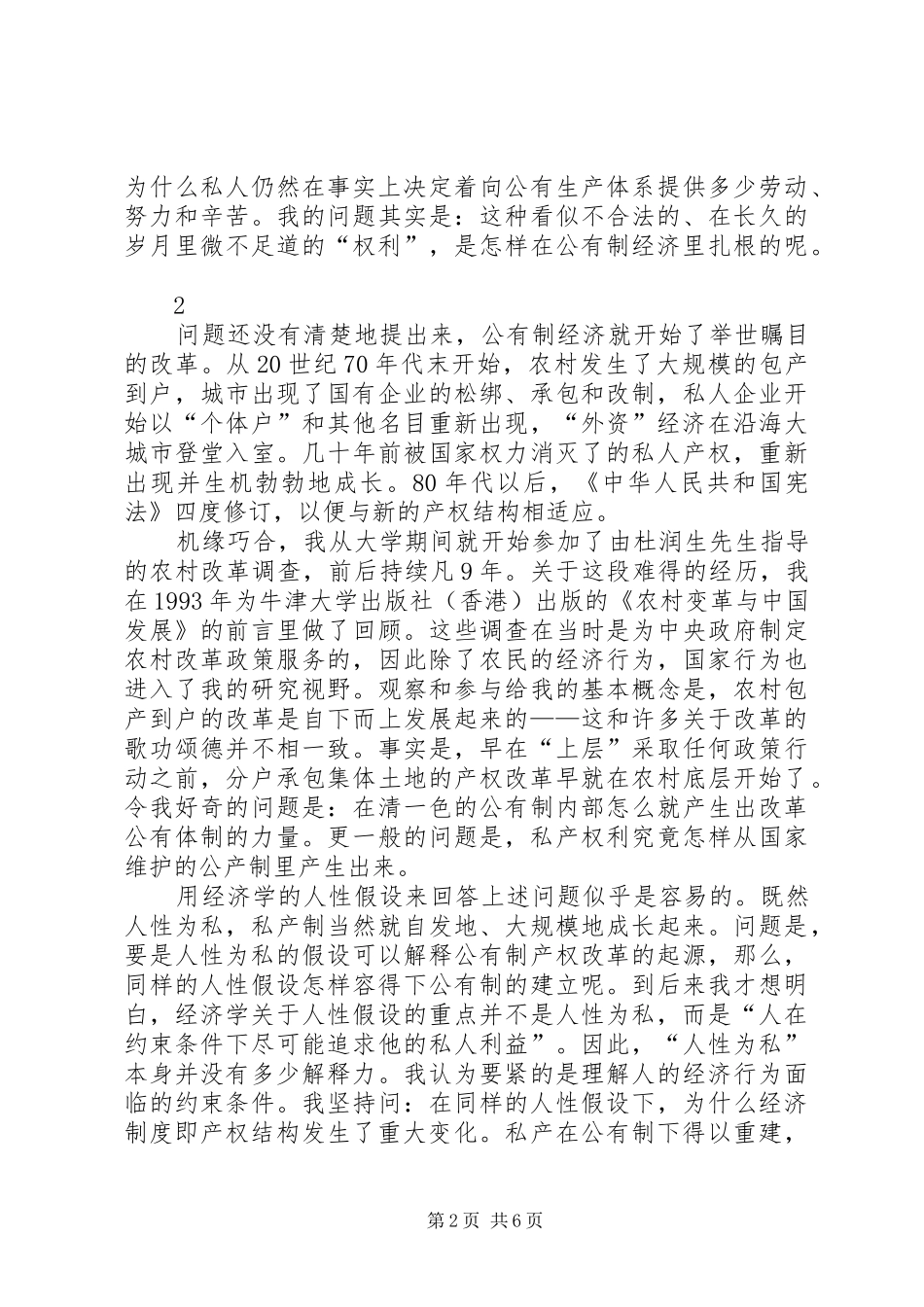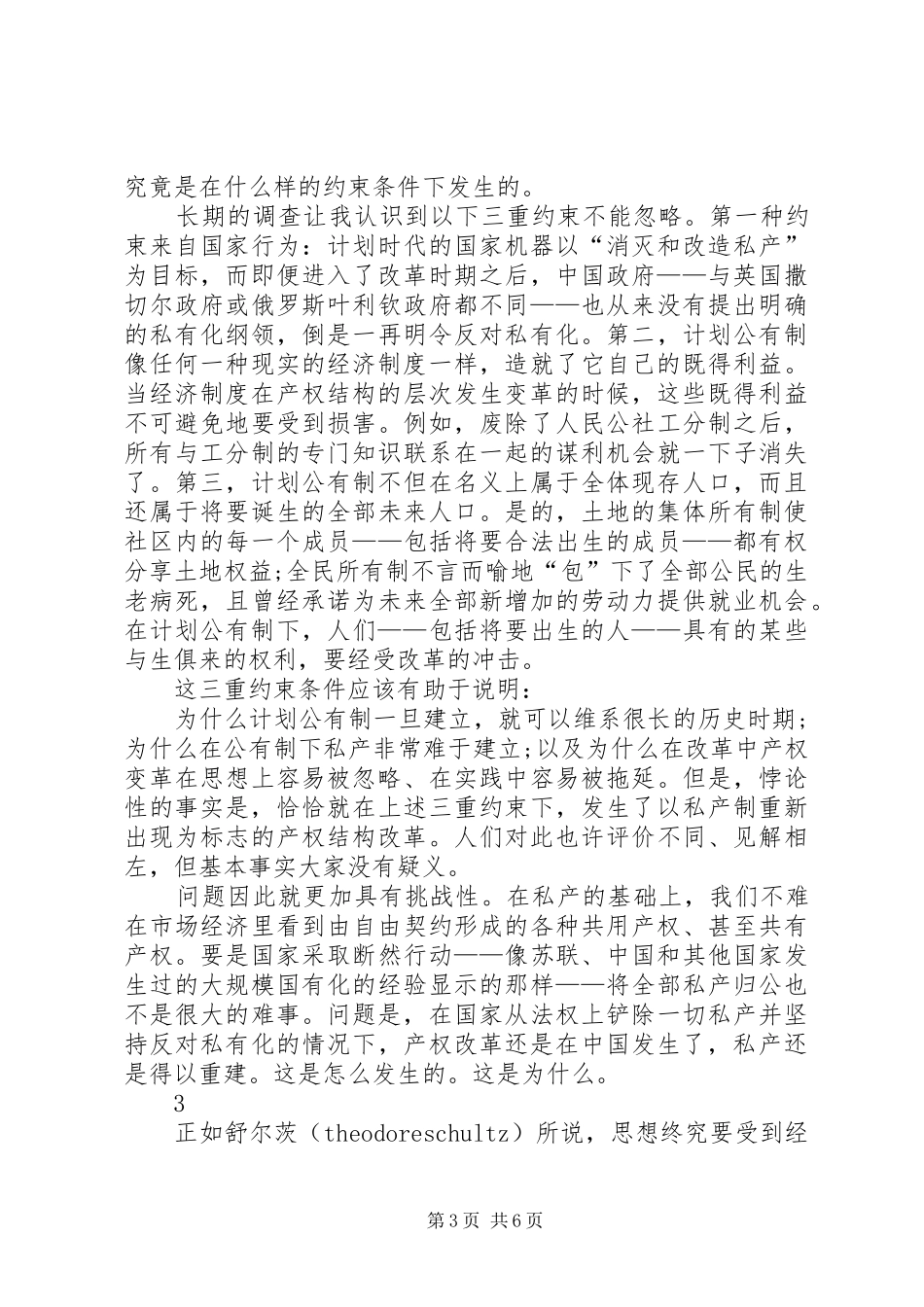产权与制度变迁周其仁除了关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篇文章之外,收入本文集的论文,全部是基于中国改革的实际经验,研究中央计划经济制度——公有制产权结构——的改革与变迁。这是近20年来我研究经济的重心所在。利用此次结集出版的机会,我要向读者简要交代一下问题的来龙去脉。1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说过,经济问题总是与选择联系在一起的。miltonfriedman(1962),pricetheory.aldinepublishingcompany,chicago.chapter1.可是,当我开始对经济问题发生兴趣的时候,惟一可观察的经济制度似乎没有任何选择性可言。是的,在中央计划公有制的体制下,生产和投资由政府指令控制,不可以自由择业,人力以外的要素也不能自主流动和重组。至于经济组织形式的选择,更事关“方向和道路”,普通人问津不得。在那个时代,“选择”——这里指的是普通的私人选择——在制度上没有合法性。要非常深入地观察和体验才有机会让我们发现,即使在不容自由选择的经济体制下,私人选择仍然顽强地存在。拿我自己1968—1978年间在黑龙江下乡时期看到的一些现象来说吧。同一个农民在“公地”与在自留地里的劳作态度判若两人,他是不是在作选择。同样的天气、地亩和劳动力数目,实施计件工资和计时工资的劳动效率大相径庭,不是劳动者在作选择又是什么。还有那朝令夕改、有时候近似胡来的“生产和投资决策”,难道可以归为公有制经济管理者的“文化水平”或“个人性情”。若是,为什么在管理者私人消费的领域,我们完全看不到类似的荒唐。说起来这是我学到的关于人的经济行为的第一课:在看似不容选择的经济制度下,人们仍然在作选择。当时我还没有可能发问:在一切资产都归公的产权制度下,为什么个人——农民、职工和管理者——仍然可以在事实上从事生产性的选择。在由“公家”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怎样生产的制度下,第1页共6页为什么私人仍然在事实上决定着向公有生产体系提供多少劳动、努力和辛苦。我的问题其实是:这种看似不合法的、在长久的岁月里微不足道的“权利”,是怎样在公有制经济里扎根的呢。2问题还没有清楚地提出来,公有制经济就开始了举世瞩目的改革。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农村发生了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城市出现了国有企业的松绑、承包和改制,私人企业开始以“个体户”和其他名目重新出现,“外资”经济在沿海大城市登堂入室。几十年前被国家权力消灭了的私人产权,重新出现并生机勃勃地成长。80年代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四度修订,以便与新的产权结构相适应。机缘巧合,我从大学期间就开始参加了由杜润生先生指导的农村改革调查,前后持续凡9年。关于这段难得的经历,我在1993年为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出版的《农村变革与中国发展》的前言里做了回顾。这些调查在当时是为中央政府制定农村改革政策服务的,因此除了农民的经济行为,国家行为也进入了我的研究视野。观察和参与给我的基本概念是,农村包产到户的改革是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这和许多关于改革的歌功颂德并不相一致。事实是,早在“上层”采取任何政策行动之前,分户承包集体土地的产权改革早就在农村底层开始了。令我好奇的问题是:在清一色的公有制内部怎么就产生出改革公有体制的力量。更一般的问题是,私产权利究竟怎样从国家维护的公产制里产生出来。用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来回答上述问题似乎是容易的。既然人性为私,私产制当然就自发地、大规模地成长起来。问题是,要是人性为私的假设可以解释公有制产权改革的起源,那么,同样的人性假设怎样容得下公有制的建立呢。到后来我才想明白,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重点并不是人性为私,而是“人在约束条件下尽可能追求他的私人利益”。因此,“人性为私”本身并没有多少解释力。我认为要紧的是理解人的经济行为面临的约束条件。我坚持问:在同样的人性假设下,为什么经济制度即产权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私产在公有制下得以重建,第2页共6页究竟是在什么样的约束条件下发生的。长期的调查让我认识到以下三重约束不能忽略。第一种约束来自国家行为:计划时代的国家机器以“消灭和改造私产”为目标,而即便进入了改革时期之后,中国政府——与英国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