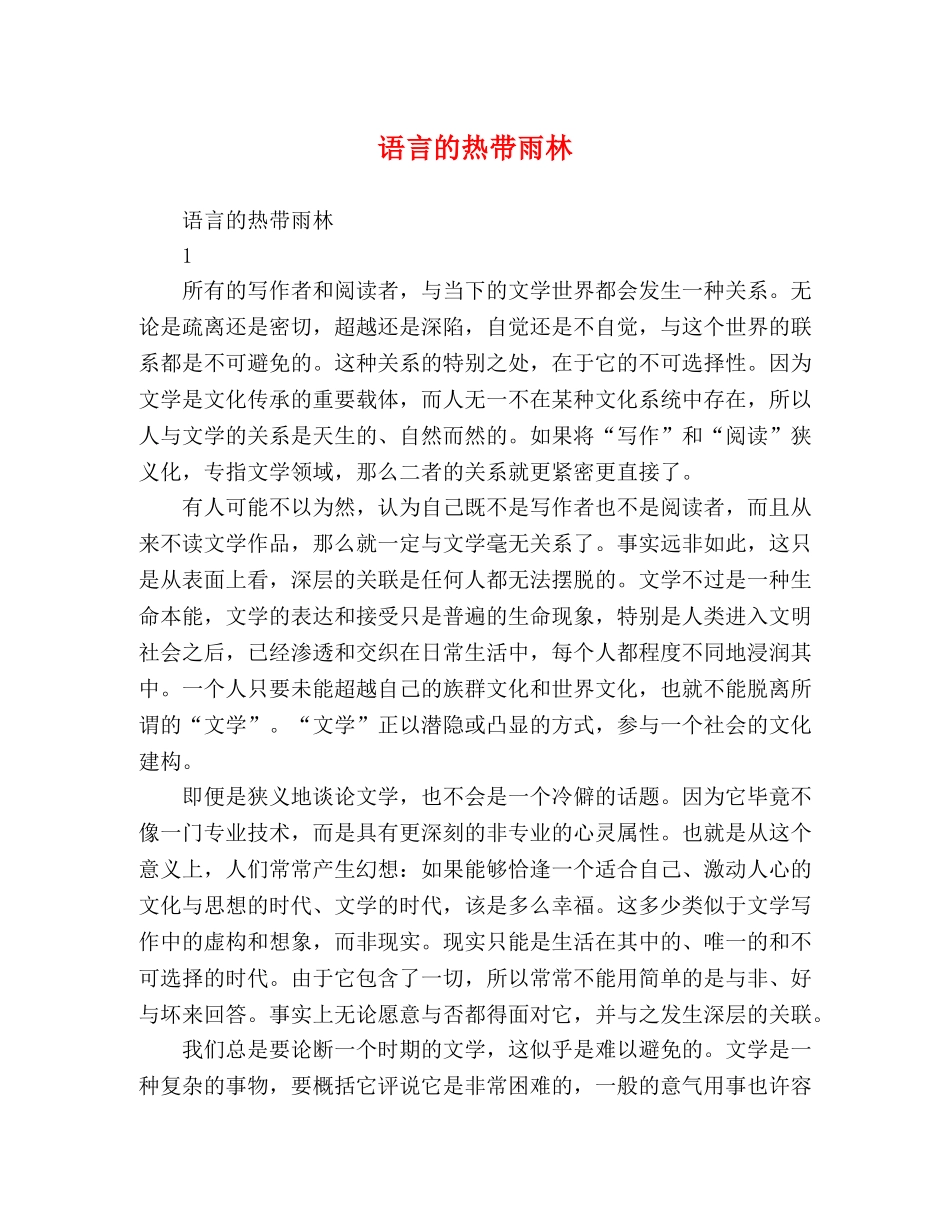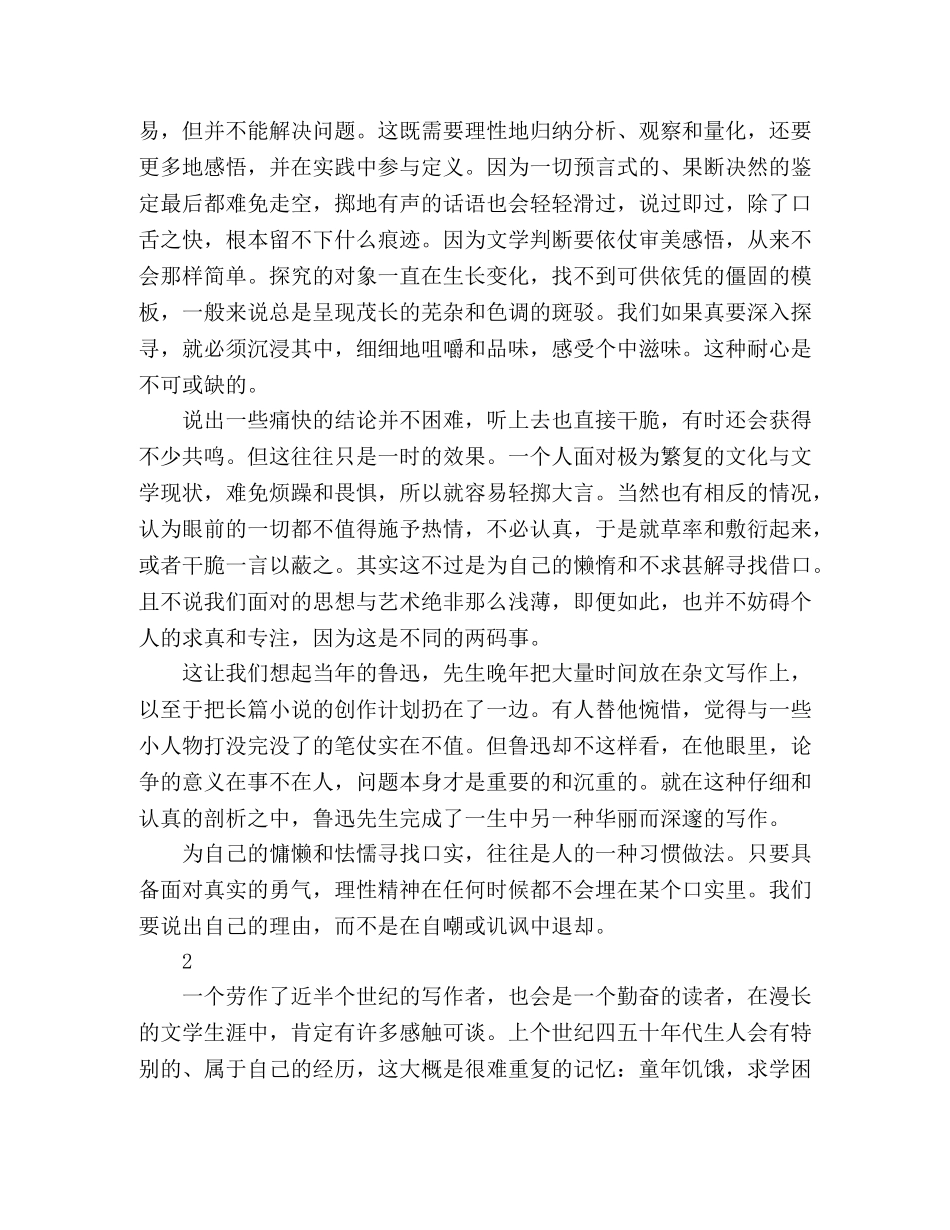语言的热带雨林语言的热带雨林1所有的写作者和阅读者,与当下的文学世界都会发生一种关系。无论是疏离还是密切,超越还是深陷,自觉还是不自觉,与这个世界的联系都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关系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不可选择性。因为文学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而人无一不在某种文化系统中存在,所以人与文学的关系是天生的、自然而然的。如果将“写作”和“阅读”狭义化,专指文学领域,那么二者的关系就更紧密更直接了。有人可能不以为然,认为自己既不是写作者也不是阅读者,而且从来不读文学作品,那么就一定与文学毫无关系了。事实远非如此,这只是从表面上看,深层的关联是任何人都无法摆脱的。文学不过是一种生命本能,文学的表达和接受只是普遍的生命现象,特别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已经渗透和交织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程度不同地浸润其中。一个人只要未能超越自己的族群文化和世界文化,也就不能脱离所谓的“文学”。“文学”正以潜隐或凸显的方式,参与一个社会的文化建构。即便是狭义地谈论文学,也不会是一个冷僻的话题。因为它毕竟不像一门专业技术,而是具有更深刻的非专业的心灵属性。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人们常常产生幻想:如果能够恰逢一个适合自己、激动人心的文化与思想的时代、文学的时代,该是多么幸福。这多少类似于文学写作中的虚构和想象,而非现实。现实只能是生活在其中的、唯一的和不可选择的时代。由于它包含了一切,所以常常不能用简单的是与非、好与坏来回答。事实上无论愿意与否都得面对它,并与之发生深层的关联。我们总是要论断一个时期的文学,这似乎是难以避免的。文学是一种复杂的事物,要概括它评说它是非常困难的,一般的意气用事也许容此资料由网络收集而来,如有侵权请告知上传者立即删除。资料共分享,我们负责传递知识。易,但并不能解决问题。这既需要理性地归纳分析、观察和量化,还要更多地感悟,并在实践中参与定义。因为一切预言式的、果断决然的鉴定最后都难免走空,掷地有声的话语也会轻轻滑过,说过即过,除了口舌之快,根本留不下什么痕迹。因为文学判断要依仗审美感悟,从来不会那样简单。探究的对象一直在生长变化,找不到可供依凭的僵固的模板,一般来说总是呈现茂长的芜杂和色调的斑驳。我们如果真要深入探寻,就必须沉浸其中,细细地咀嚼和品味,感受个中滋味。这种耐心是不可或缺的。说出一些痛快的结论并不困难,听上去也直接干脆,有时还会获得不少共鸣。但这往往只是一时的效果。一个人面对极为繁复的文化与文学现状,难免烦躁和畏惧,所以就容易轻掷大言。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认为眼前的一切都不值得施予热情,不必认真,于是就草率和敷衍起来,或者干脆一言以蔽之。其实这不过是为自己的懒惰和不求甚解寻找借口。且不说我们面对的思想与艺术绝非那么浅薄,即便如此,也并不妨碍个人的求真和专注,因为这是不同的两码事。这让我们想起当年的鲁迅,先生晚年把大量时间放在杂文写作上,以至于把长篇小说的创作计划扔在了一边。有人替他惋惜,觉得与一些小人物打没完没了的笔仗实在不值。但鲁迅却不这样看,在他眼里,论争的意义在事不在人,问题本身才是重要的和沉重的。就在这种仔细和认真的剖析之中,鲁迅先生完成了一生中另一种华丽而深邃的写作。为自己的慵懒和怯懦寻找口实,往往是人的一种习惯做法。只要具备面对真实的勇气,理性精神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埋在某个口实里。我们要说出自己的理由,而不是在自嘲或讥讽中退却。2一个劳作了近半个世纪的写作者,也会是一个勤奋的读者,在漫长的文学生涯中,肯定有许多感触可谈。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生人会有特别的、属于自己的经历,这大概是很难重复的记忆:童年饥饿,求学困此资料由网络收集而来,如有侵权请告知上传者立即删除。资料共分享,我们负责传递知识。难,“上山下乡”和“文革”等,一路走来的许多重大社会变动跌宕,不可谓不大。后来又是对外开放时期,是商业化网络化时代。文学在剧烈起伏的社会思潮中演变,高潮低潮,前进倒退,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楚的。记忆中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年最多出版三两部长篇小说,散文和短篇小说集也只有不多几部,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