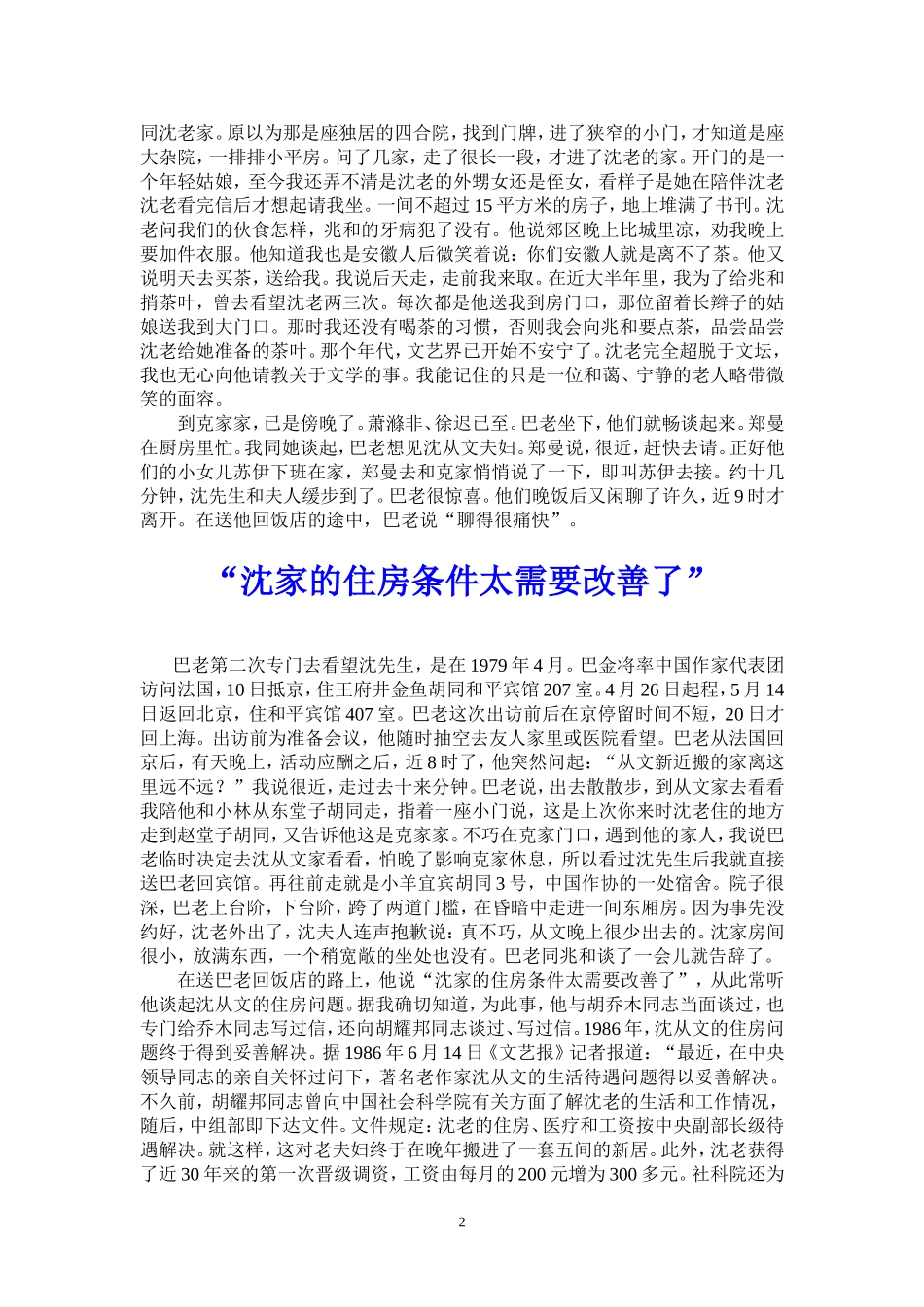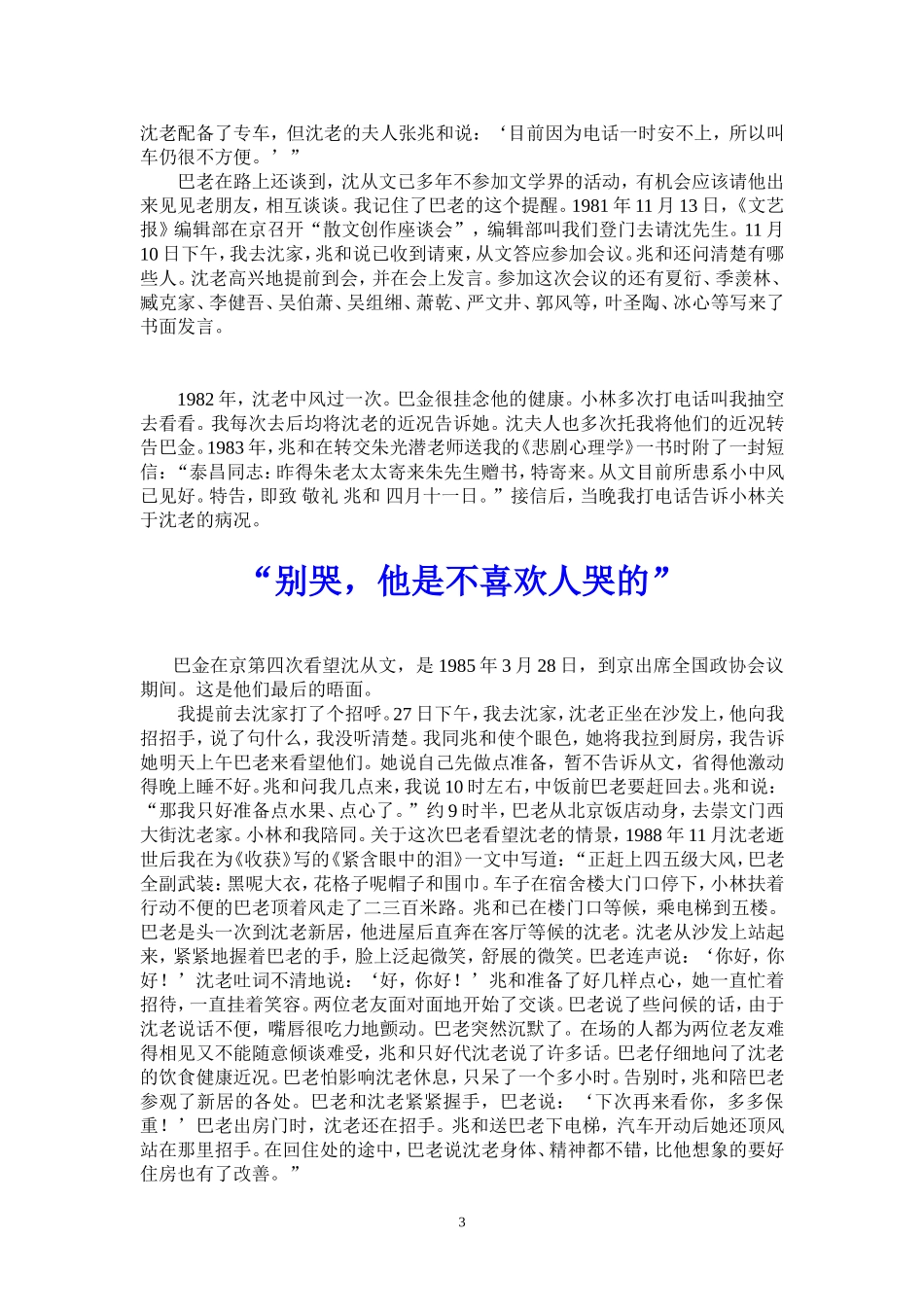文学大师巴金与沈从文的最后晤面吴泰昌挚友相见,“聊得很痛快”巴金与沈从文是挚友。1974年,沈从文、张兆和夫妇在上海看望过巴金,巴金其时尚未结束“审查”。就我的记忆,巴老“文革”结束后来京,曾四次去看望沈从文,一次是在臧克家家中,一次夜访未遇,第四届文代会期间又去小羊宜宾胡同相访未遇,最后一次是在沈家。1978年2月24日,巴金到达北京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住西苑饭店。在会议上,巴金见到茅盾、冰心、叶圣陶、胡愈之、曹禺等老友,大家都是10多年不见了。会议结束后,他想看看朋友,将女儿李小林叫来陪他。3月8日,经周而复安排,巴老父女迁到前门饭店357号的一个套间房。次日,他们便开始频繁的访友活动。小林与我商量,有几处也请我陪陪。11日下午,巴老去臧克家家。巴金与克家从1977年4月起已恢复书信联系,巴老还代小林他们的《浙江文艺》向克家要过两首诗。10日晚,我专门去了克家家,转告他明天下午巴金来看他。克家和夫人郑曼当即决定明晚请巴老吃饭。克家说,主要是叙叙,就在家里吃吧,再约上当时在京的萧滌非、徐迟。山东大学教授萧滌非是克家的老乡,克家任《诗刊》主编时,徐迟任副主编。小林约好,当天下午我在《人民文学》办公室等她的电话。下午3时多,突然接到沙汀的电话,说巴老在张天翼家,叫我用车去接。天翼当时因脑血栓半身不遂,行动谈吐不便,靠打手势交流。我与天翼在干校同在一个连队,回京后又同住大佛寺一所宅院,他住正房,我住厕所隔壁的一间厢房。他夫人沈承宽和我是《文艺报》的同仁。我坐《人民文学》的车到天翼家,巴老、沙汀正要起身。按计划,从天翼家出来,先去夏衍家。也是头天晚上,我从克家家出来骑车到夏公家告诉他。夏公问我巴金能呆多久,我说从您家出来再到克家处,他说:“这样我就不准备留他吃饭了。”巴金在夏公家坐了不到一小时。他们彼此问候,夏公问了上海一些朋友的近况。夏公拄着拐杖送巴金到大门口。在去克家处的路上,巴老突然问我:“从文家离克家家远不远?”我说很近几百米。我知道巴老想见沈先生。是在克家家见,还是从克家家出来再去沈家?巴老没说。我第一次见到沈老,介绍人是沈夫人。1964年春天我到《文艺报》工作,已听说沈夫人张兆和在人民文学杂志社,和我在同一幢大楼里。我认识她,她并不认识我。1965年我去京郊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兆和在一个生产队,开始有了接触。她知道我是安徽老乡,又是北大出来的,渐渐交谈起来。因工作关系,个把月我能回趟北京。有次我正走出村口,她在后面叫我,匆匆地递给我一封信,请我去她家看望一下沈先生,捎回来一点茶叶。看了信封上的地址,我心里一愣,原来沈先生家离我家住处很近。当天晚上,我在浴室里洗了个痛快澡,就去东堂子胡1同沈老家。原以为那是座独居的四合院,找到门牌,进了狭窄的小门,才知道是座大杂院,一排排小平房。问了几家,走了很长一段,才进了沈老的家。开门的是一个年轻姑娘,至今我还弄不清是沈老的外甥女还是侄女,看样子是她在陪伴沈老沈老看完信后才想起请我坐。一间不超过15平方米的房子,地上堆满了书刊。沈老问我们的伙食怎样,兆和的牙病犯了没有。他说郊区晚上比城里凉,劝我晚上要加件衣服。他知道我也是安徽人后微笑着说:你们安徽人就是离不了茶。他又说明天去买茶,送给我。我说后天走,走前我来取。在近大半年里,我为了给兆和捎茶叶,曾去看望沈老两三次。每次都是他送我到房门口,那位留着长辫子的姑娘送我到大门口。那时我还没有喝茶的习惯,否则我会向兆和要点茶,品尝品尝沈老给她准备的茶叶。那个年代,文艺界已开始不安宁了。沈老完全超脱于文坛,我也无心向他请教关于文学的事。我能记住的只是一位和蔼、宁静的老人略带微笑的面容。到克家家,已是傍晚了。萧滌非、徐迟已至。巴老坐下,他们就畅谈起来。郑曼在厨房里忙。我同她谈起,巴老想见沈从文夫妇。郑曼说,很近,赶快去请。正好他们的小女儿苏伊下班在家,郑曼去和克家悄悄说了一下,即叫苏伊去接。约十几分钟,沈先生和夫人缓步到了。巴老很惊喜。他们晚饭后又闲聊了许久,近9时才离开。在送他回饭店的途中,巴老说“聊得很痛快”。“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