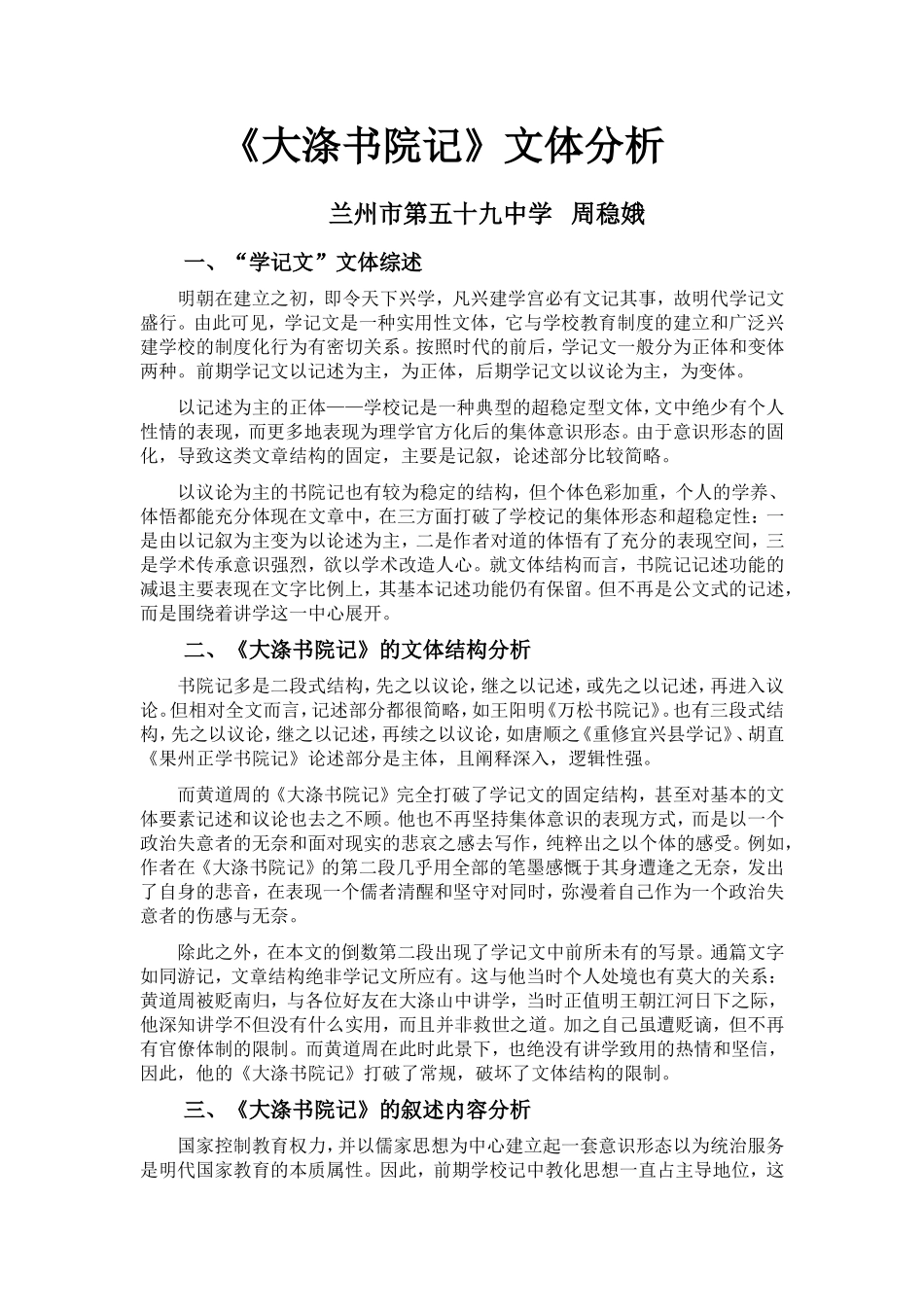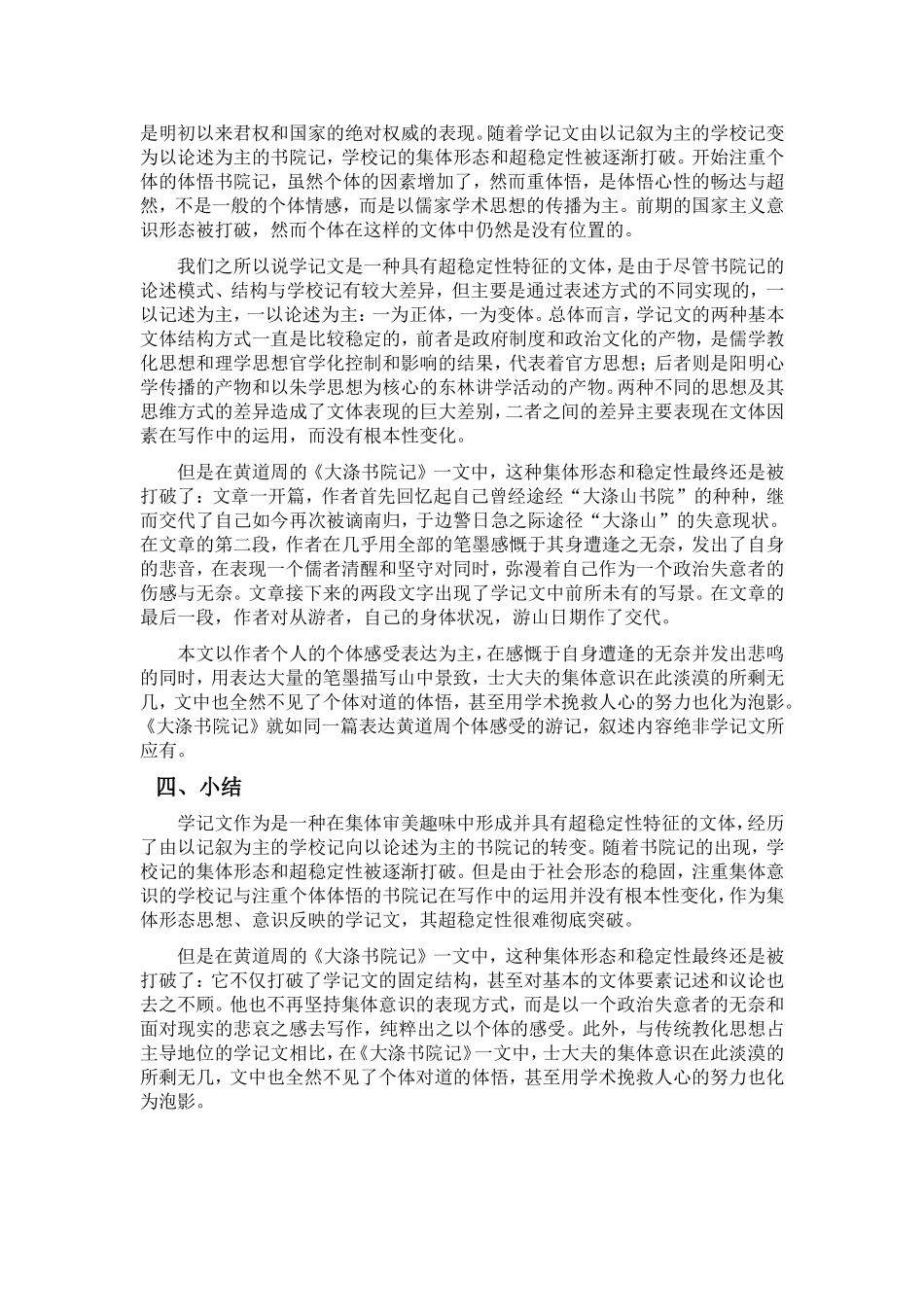《大涤书院记》文体分析兰州市第五十九中学周稳娥一、“学记文”文体综述明朝在建立之初,即令天下兴学,凡兴建学宫必有文记其事,故明代学记文盛行。由此可见,学记文是一种实用性文体,它与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广泛兴建学校的制度化行为有密切关系。按照时代的前后,学记文一般分为正体和变体两种。前期学记文以记述为主,为正体,后期学记文以议论为主,为变体。以记述为主的正体——学校记是一种典型的超稳定型文体,文中绝少有个人性情的表现,而更多地表现为理学官方化后的集体意识形态。由于意识形态的固化,导致这类文章结构的固定,主要是记叙,论述部分比较简略。以议论为主的书院记也有较为稳定的结构,但个体色彩加重,个人的学养、体悟都能充分体现在文章中,在三方面打破了学校记的集体形态和超稳定性:一是由以记叙为主变为以论述为主,二是作者对道的体悟有了充分的表现空间,三是学术传承意识强烈,欲以学术改造人心。就文体结构而言,书院记记述功能的减退主要表现在文字比例上,其基本记述功能仍有保留。但不再是公文式的记述,而是围绕着讲学这一中心展开。二、《大涤书院记》的文体结构分析书院记多是二段式结构,先之以议论,继之以记述,或先之以记述,再进入议论。但相对全文而言,记述部分都很简略,如王阳明《万松书院记》。也有三段式结构,先之以议论,继之以记述,再续之以议论,如唐顺之《重修宜兴县学记》、胡直《果州正学书院记》论述部分是主体,且阐释深入,逻辑性强。而黄道周的《大涤书院记》完全打破了学记文的固定结构,甚至对基本的文体要素记述和议论也去之不顾。他也不再坚持集体意识的表现方式,而是以一个政治失意者的无奈和面对现实的悲哀之感去写作,纯粹出之以个体的感受。例如,作者在《大涤书院记》的第二段几乎用全部的笔墨感慨于其身遭逢之无奈,发出了自身的悲音,在表现一个儒者清醒和坚守对同时,弥漫着自己作为一个政治失意者的伤感与无奈。除此之外,在本文的倒数第二段出现了学记文中前所未有的写景。通篇文字如同游记,文章结构绝非学记文所应有。这与他当时个人处境也有莫大的关系:黄道周被贬南归,与各位好友在大涤山中讲学,当时正值明王朝江河日下之际,他深知讲学不但没有什么实用,而且并非救世之道。加之自己虽遭贬谪,但不再有官僚体制的限制。而黄道周在此时此景下,也绝没有讲学致用的热情和坚信,因此,他的《大涤书院记》打破了常规,破坏了文体结构的限制。三、《大涤书院记》的叙述内容分析国家控制教育权力,并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建立起一套意识形态以为统治服务是明代国家教育的本质属性。因此,前期学校记中教化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这是明初以来君权和国家的绝对权威的表现。随着学记文由以记叙为主的学校记变为以论述为主的书院记,学校记的集体形态和超稳定性被逐渐打破。开始注重个体的体悟书院记,虽然个体的因素增加了,然而重体悟,是体悟心性的畅达与超然,不是一般的个体情感,而是以儒家学术思想的传播为主。前期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被打破,然而个体在这样的文体中仍然是没有位置的。我们之所以说学记文是一种具有超稳定性特征的文体,是由于尽管书院记的论述模式、结构与学校记有较大差异,但主要是通过表述方式的不同实现的,一以记述为主,一以论述为主:一为正体,一为变体。总体而言,学记文的两种基本文体结构方式一直是比较稳定的,前者是政府制度和政治文化的产物,是儒学教化思想和理学思想官学化控制和影响的结果,代表着官方思想;后者则是阳明心学传播的产物和以朱学思想为核心的东林讲学活动的产物。两种不同的思想及其思维方式的差异造成了文体表现的巨大差别,二者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文体因素在写作中的运用,而没有根本性变化。但是在黄道周的《大涤书院记》一文中,这种集体形态和稳定性最终还是被打破了:文章一开篇,作者首先回忆起自己曾经途经“大涤山书院”的种种,继而交代了自己如今再次被谪南归,于边警日急之际途径“大涤山”的失意现状。在文章的第二段,作者在几乎用全部的笔墨感慨于其身遭逢之无奈,发出了自身的悲音,在表现一个儒者清醒和坚守对同时,弥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