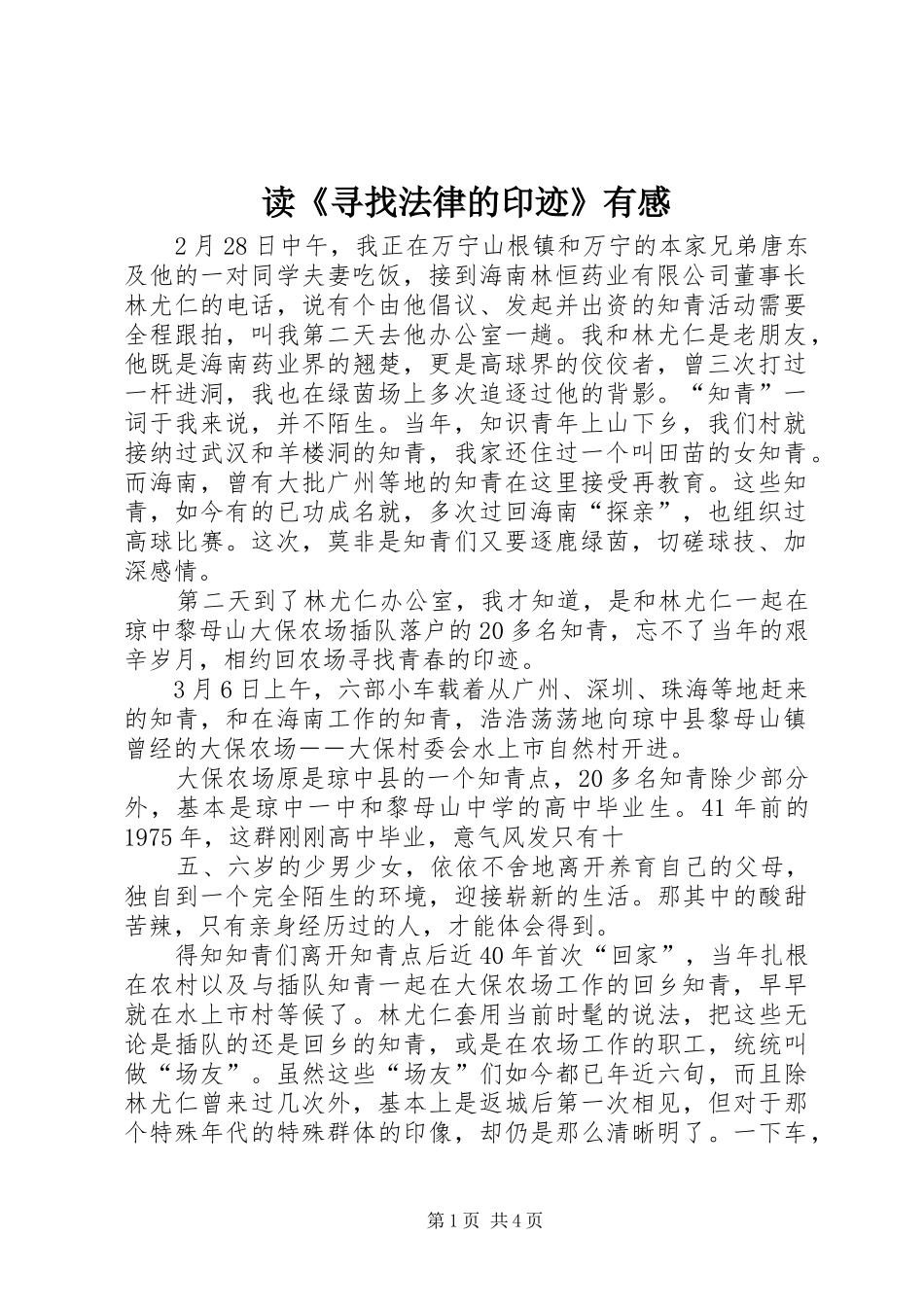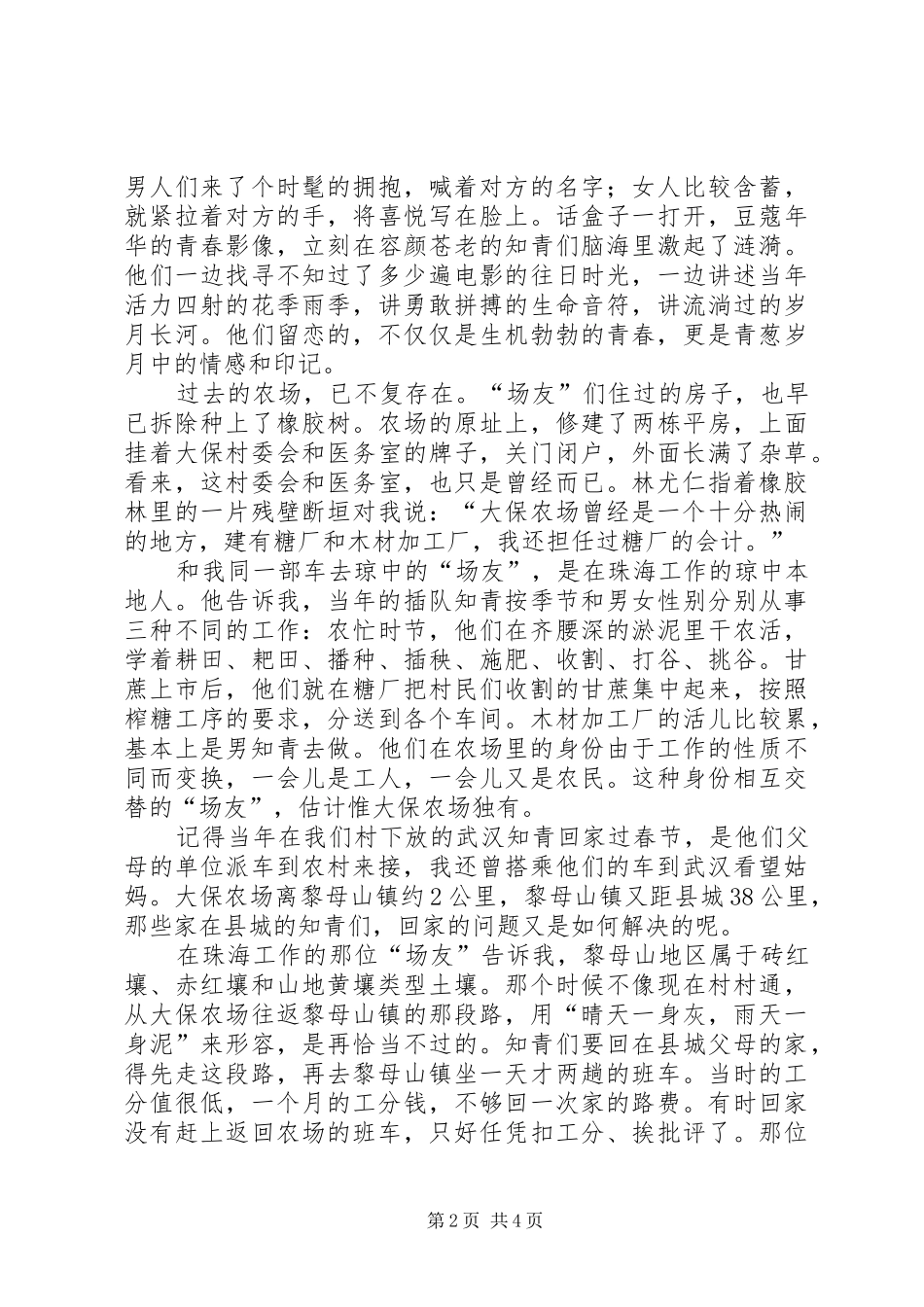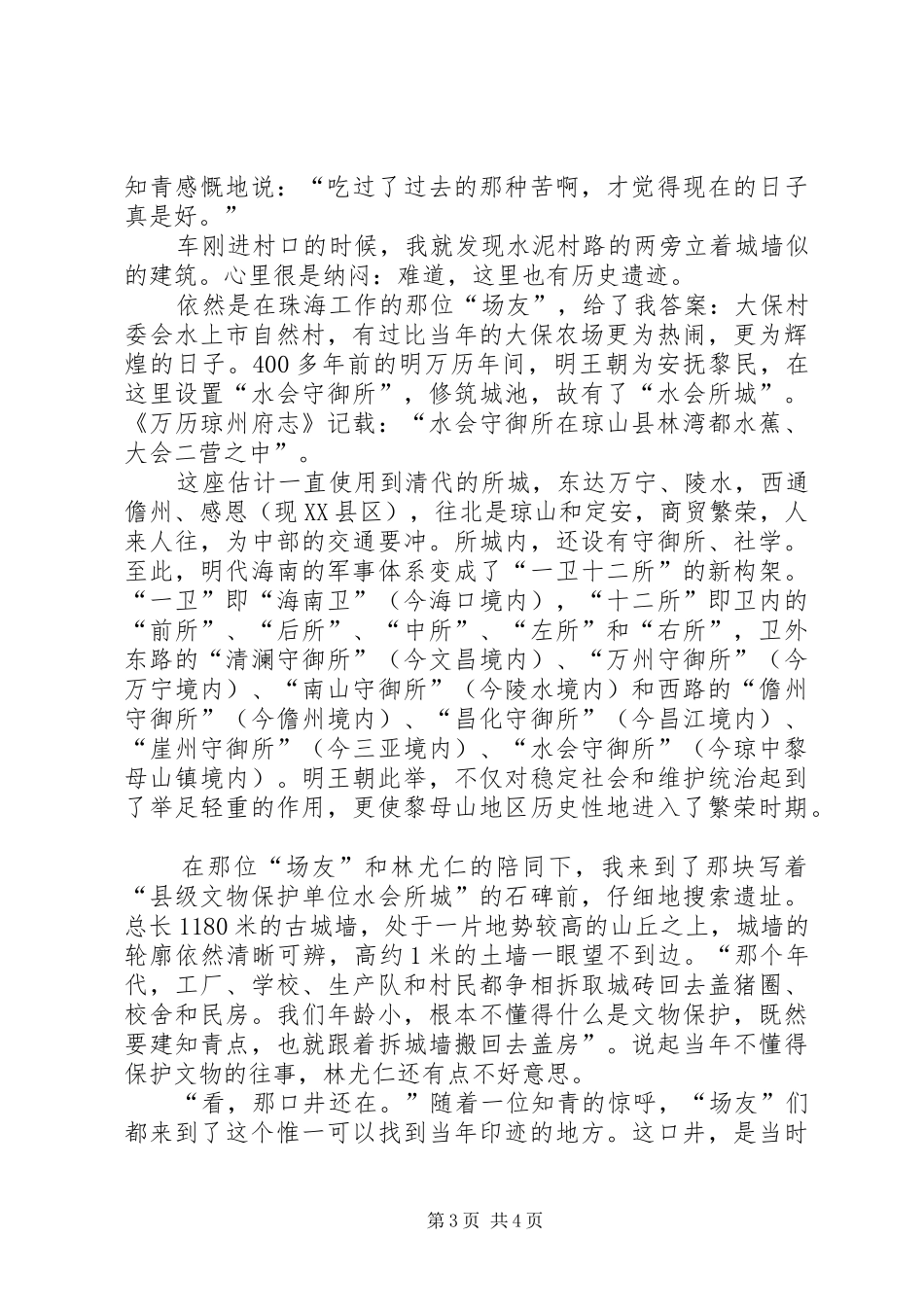读《寻找法律的印迹》有感2月28日中午,我正在万宁山根镇和万宁的本家兄弟唐东及他的一对同学夫妻吃饭,接到海南林恒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尤仁的电话,说有个由他倡议、发起并出资的知青活动需要全程跟拍,叫我第二天去他办公室一趟。我和林尤仁是老朋友,他既是海南药业界的翘楚,更是高球界的佼佼者,曾三次打过一杆进洞,我也在绿茵场上多次追逐过他的背影。“知青”一词于我来说,并不陌生。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们村就接纳过武汉和羊楼洞的知青,我家还住过一个叫田苗的女知青。而海南,曾有大批广州等地的知青在这里接受再教育。这些知青,如今有的已功成名就,多次过回海南“探亲”,也组织过高球比赛。这次,莫非是知青们又要逐鹿绿茵,切磋球技、加深感情。第二天到了林尤仁办公室,我才知道,是和林尤仁一起在琼中黎母山大保农场插队落户的20多名知青,忘不了当年的艰辛岁月,相约回农场寻找青春的印迹。3月6日上午,六部小车载着从广州、深圳、珠海等地赶来的知青,和在海南工作的知青,浩浩荡荡地向琼中县黎母山镇曾经的大保农场--大保村委会水上市自然村开进。大保农场原是琼中县的一个知青点,20多名知青除少部分外,基本是琼中一中和黎母山中学的高中毕业生。41年前的1975年,这群刚刚高中毕业,意气风发只有十五、六岁的少男少女,依依不舍地离开养育自己的父母,独自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迎接崭新的生活。那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得到。得知知青们离开知青点后近40年首次“回家”,当年扎根在农村以及与插队知青一起在大保农场工作的回乡知青,早早就在水上市村等候了。林尤仁套用当前时髦的说法,把这些无论是插队的还是回乡的知青,或是在农场工作的职工,统统叫做“场友”。虽然这些“场友”们如今都已年近六旬,而且除林尤仁曾来过几次外,基本上是返城后第一次相见,但对于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群体的印像,却仍是那么清晰明了。一下车,第1页共4页男人们来了个时髦的拥抱,喊着对方的名字;女人比较含蓄,就紧拉着对方的手,将喜悦写在脸上。话盒子一打开,豆蔻年华的青春影像,立刻在容颜苍老的知青们脑海里激起了涟漪。他们一边找寻不知过了多少遍电影的往日时光,一边讲述当年活力四射的花季雨季,讲勇敢拼搏的生命音符,讲流淌过的岁月长河。他们留恋的,不仅仅是生机勃勃的青春,更是青葱岁月中的情感和印记。过去的农场,已不复存在。“场友”们住过的房子,也早已拆除种上了橡胶树。农场的原址上,修建了两栋平房,上面挂着大保村委会和医务室的牌子,关门闭户,外面长满了杂草。看来,这村委会和医务室,也只是曾经而已。林尤仁指着橡胶林里的一片残壁断垣对我说:“大保农场曾经是一个十分热闹的地方,建有糖厂和木材加工厂,我还担任过糖厂的会计。”和我同一部车去琼中的“场友”,是在珠海工作的琼中本地人。他告诉我,当年的插队知青按季节和男女性别分别从事三种不同的工作:农忙时节,他们在齐腰深的淤泥里干农活,学着耕田、耙田、播种、插秧、施肥、收割、打谷、挑谷。甘蔗上市后,他们就在糖厂把村民们收割的甘蔗集中起来,按照榨糖工序的要求,分送到各个车间。木材加工厂的活儿比较累,基本上是男知青去做。他们在农场里的身份由于工作的性质不同而变换,一会儿是工人,一会儿又是农民。这种身份相互交替的“场友”,估计惟大保农场独有。记得当年在我们村下放的武汉知青回家过春节,是他们父母的单位派车到农村来接,我还曾搭乘他们的车到武汉看望姑妈。大保农场离黎母山镇约2公里,黎母山镇又距县城38公里,那些家在县城的知青们,回家的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呢。在珠海工作的那位“场友”告诉我,黎母山地区属于砖红壤、赤红壤和山地黄壤类型土壤。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村村通,从大保农场往返黎母山镇的那段路,用“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的。知青们要回在县城父母的家,得先走这段路,再去黎母山镇坐一天才两趟的班车。当时的工分值很低,一个月的工分钱,不够回一次家的路费。有时回家没有赶上返回农场的班车,只好任凭扣工分、挨批评了。那位第2页共4页知青感慨地说:“吃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