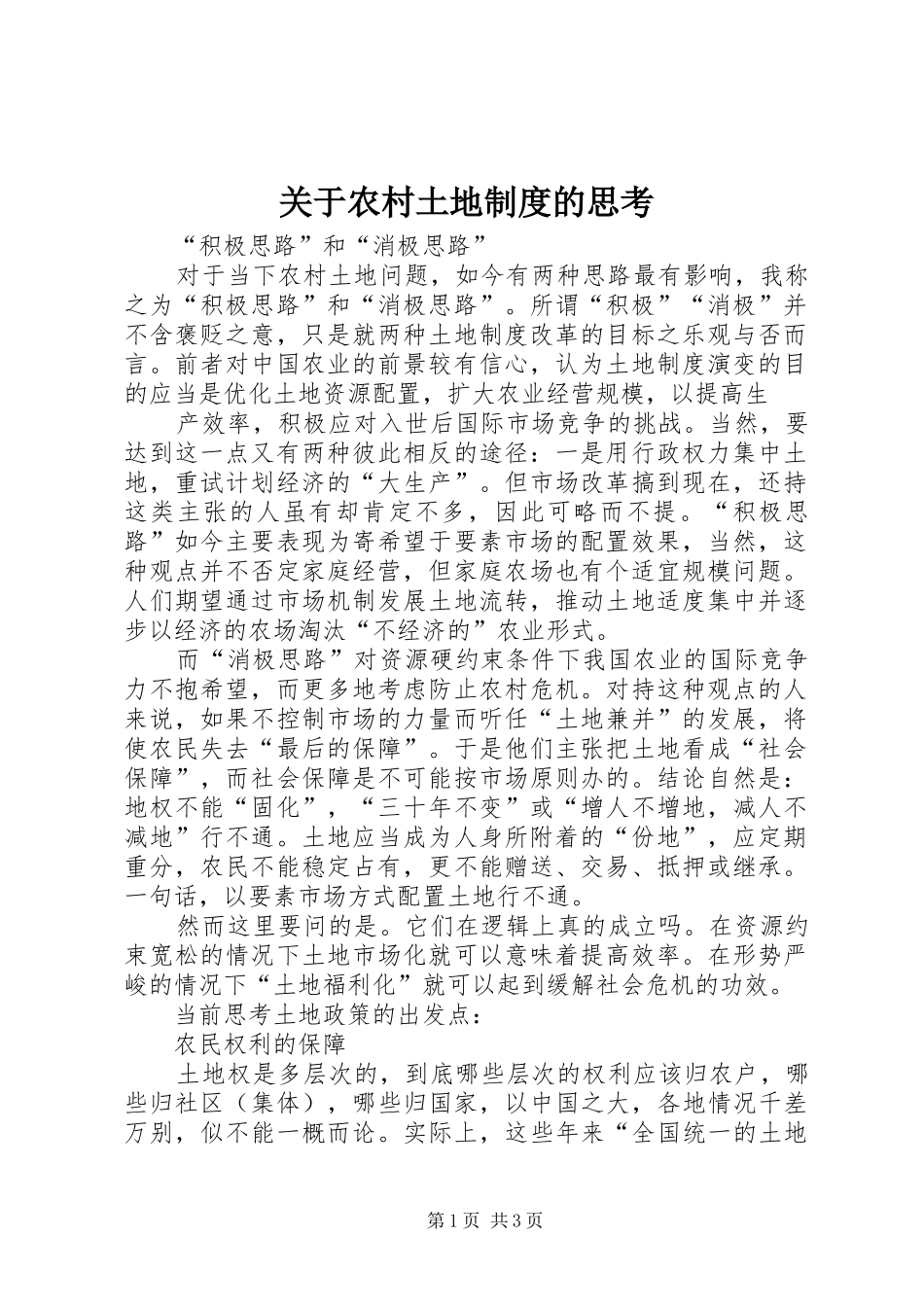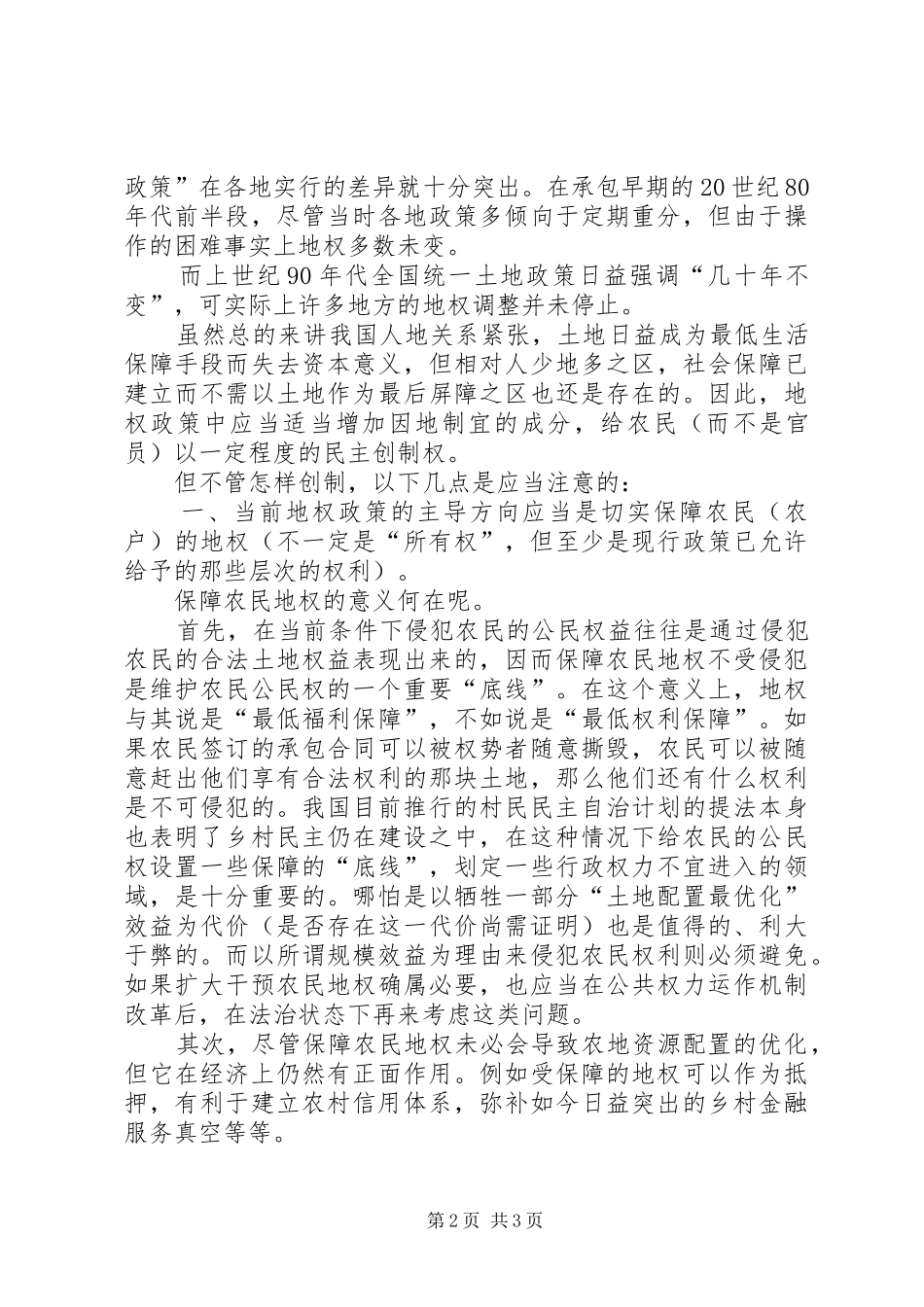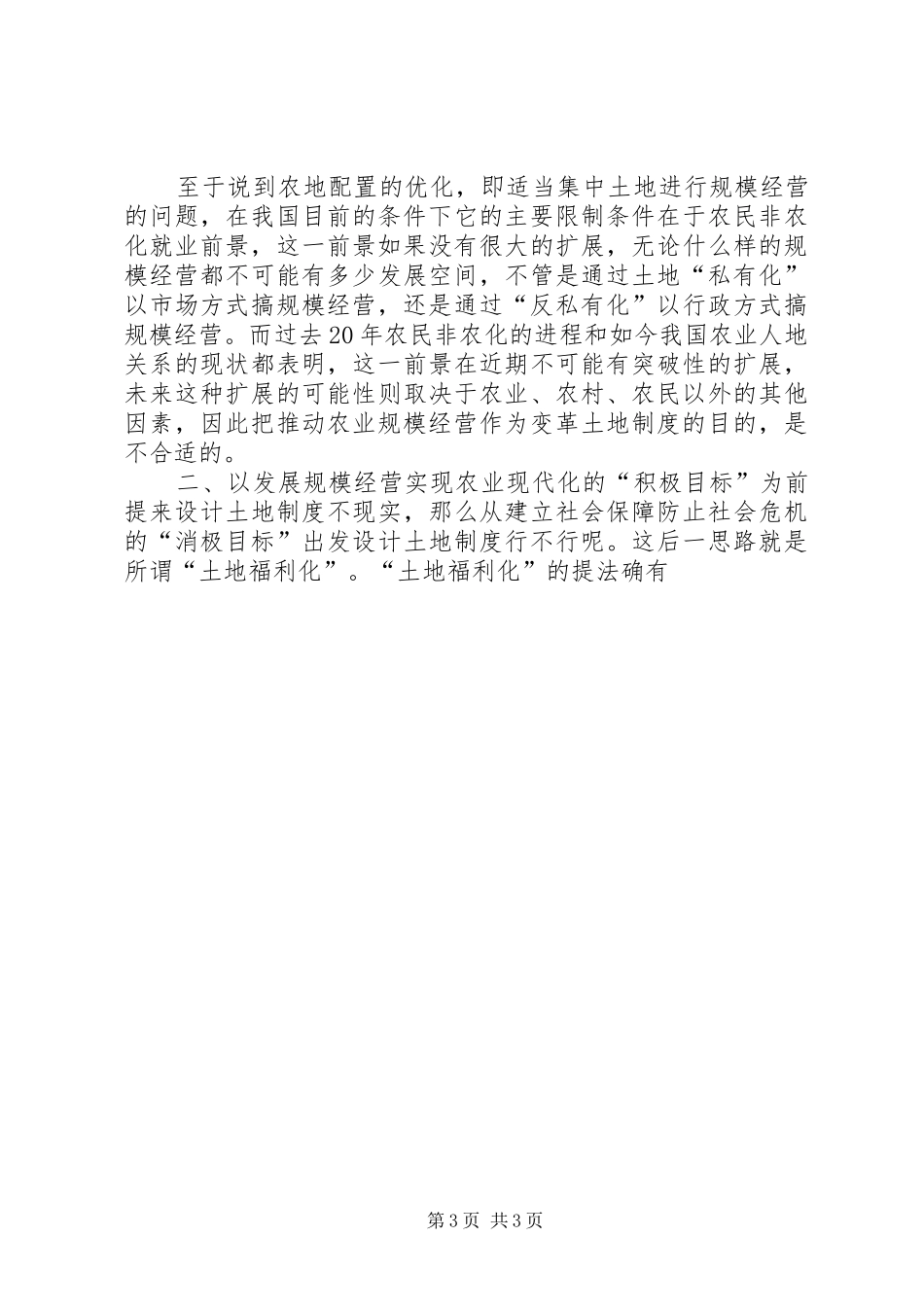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思考“积极思路”和“消极思路”对于当下农村土地问题,如今有两种思路最有影响,我称之为“积极思路”和“消极思路”。所谓“积极”“消极”并不含褒贬之意,只是就两种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之乐观与否而言。前者对中国农业的前景较有信心,认为土地制度演变的目的应当是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扩大农业经营规模,以提高生产效率,积极应对入世后国际市场竞争的挑战。当然,要达到这一点又有两种彼此相反的途径:一是用行政权力集中土地,重试计划经济的“大生产”。但市场改革搞到现在,还持这类主张的人虽有却肯定不多,因此可略而不提。“积极思路”如今主要表现为寄希望于要素市场的配置效果,当然,这种观点并不否定家庭经营,但家庭农场也有个适宜规模问题。人们期望通过市场机制发展土地流转,推动土地适度集中并逐步以经济的农场淘汰“不经济的”农业形式。而“消极思路”对资源硬约束条件下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抱希望,而更多地考虑防止农村危机。对持这种观点的人来说,如果不控制市场的力量而听任“土地兼并”的发展,将使农民失去“最后的保障”。于是他们主张把土地看成“社会保障”,而社会保障是不可能按市场原则办的。结论自然是:地权不能“固化”,“三十年不变”或“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行不通。土地应当成为人身所附着的“份地”,应定期重分,农民不能稳定占有,更不能赠送、交易、抵押或继承。一句话,以要素市场方式配置土地行不通。然而这里要问的是。它们在逻辑上真的成立吗。在资源约束宽松的情况下土地市场化就可以意味着提高效率。在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土地福利化”就可以起到缓解社会危机的功效。当前思考土地政策的出发点:农民权利的保障土地权是多层次的,到底哪些层次的权利应该归农户,哪些归社区(集体),哪些归国家,以中国之大,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似不能一概而论。实际上,这些年来“全国统一的土地第1页共3页政策”在各地实行的差异就十分突出。在承包早期的20世纪80年代前半段,尽管当时各地政策多倾向于定期重分,但由于操作的困难事实上地权多数未变。而上世纪90年代全国统一土地政策日益强调“几十年不变”,可实际上许多地方的地权调整并未停止。虽然总的来讲我国人地关系紧张,土地日益成为最低生活保障手段而失去资本意义,但相对人少地多之区,社会保障已建立而不需以土地作为最后屏障之区也还是存在的。因此,地权政策中应当适当增加因地制宜的成分,给农民(而不是官员)以一定程度的民主创制权。但不管怎样创制,以下几点是应当注意的:一、当前地权政策的主导方向应当是切实保障农民(农户)的地权(不一定是“所有权”,但至少是现行政策已允许给予的那些层次的权利)。保障农民地权的意义何在呢。首先,在当前条件下侵犯农民的公民权益往往是通过侵犯农民的合法土地权益表现出来的,因而保障农民地权不受侵犯是维护农民公民权的一个重要“底线”。在这个意义上,地权与其说是“最低福利保障”,不如说是“最低权利保障”。如果农民签订的承包合同可以被权势者随意撕毁,农民可以被随意赶出他们享有合法权利的那块土地,那么他们还有什么权利是不可侵犯的。我国目前推行的村民民主自治计划的提法本身也表明了乡村民主仍在建设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给农民的公民权设置一些保障的“底线”,划定一些行政权力不宜进入的领域,是十分重要的。哪怕是以牺牲一部分“土地配置最优化”效益为代价(是否存在这一代价尚需证明)也是值得的、利大于弊的。而以所谓规模效益为理由来侵犯农民权利则必须避免。如果扩大干预农民地权确属必要,也应当在公共权力运作机制改革后,在法治状态下再来考虑这类问题。其次,尽管保障农民地权未必会导致农地资源配置的优化,但它在经济上仍然有正面作用。例如受保障的地权可以作为抵押,有利于建立农村信用体系,弥补如今日益突出的乡村金融服务真空等等。第2页共3页至于说到农地配置的优化,即适当集中土地进行规模经营的问题,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它的主要限制条件在于农民非农化就业前景,这一前景如果没有很大的扩展,无论什么样的规模经营都不可能有多少发展空间,不管是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