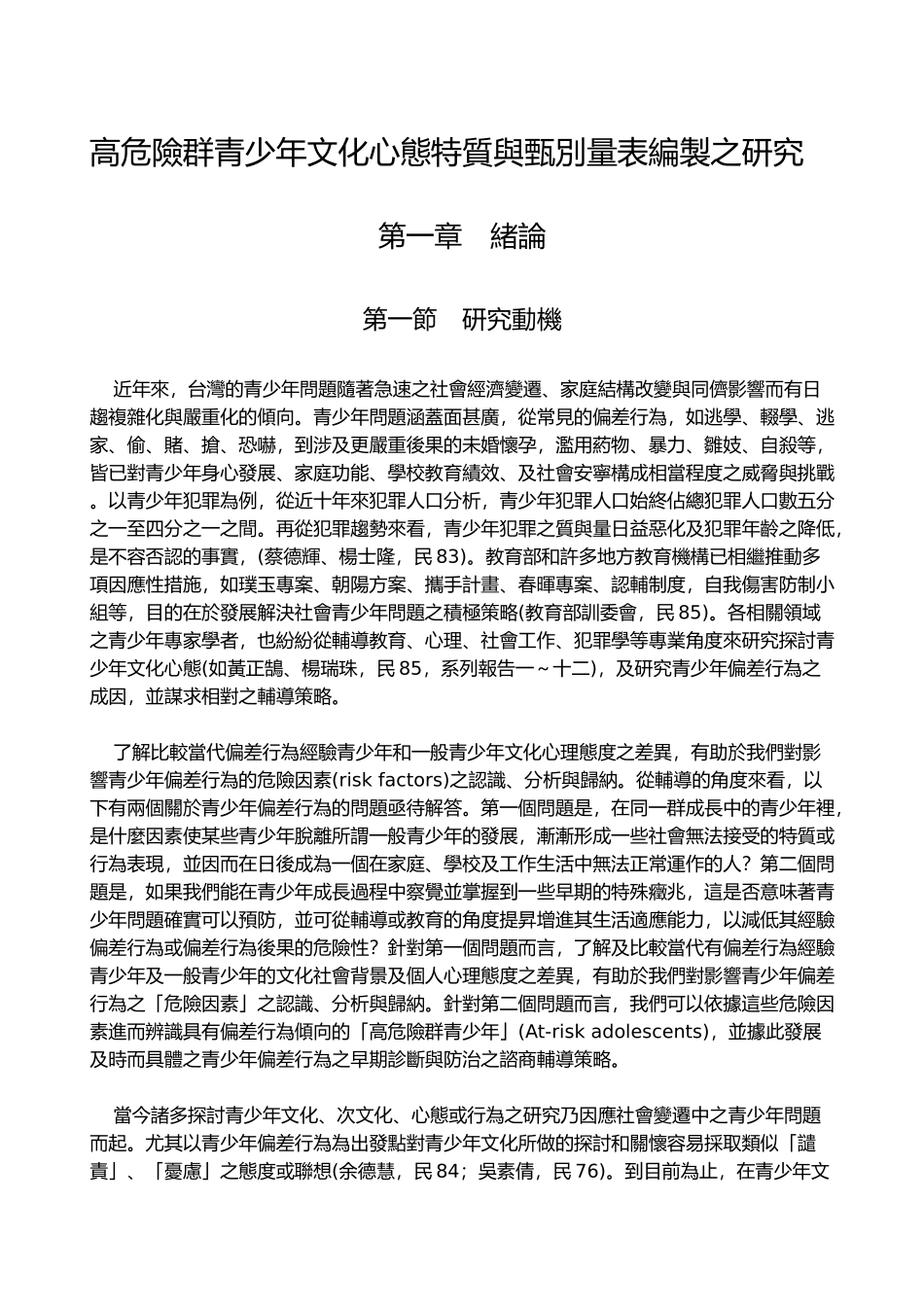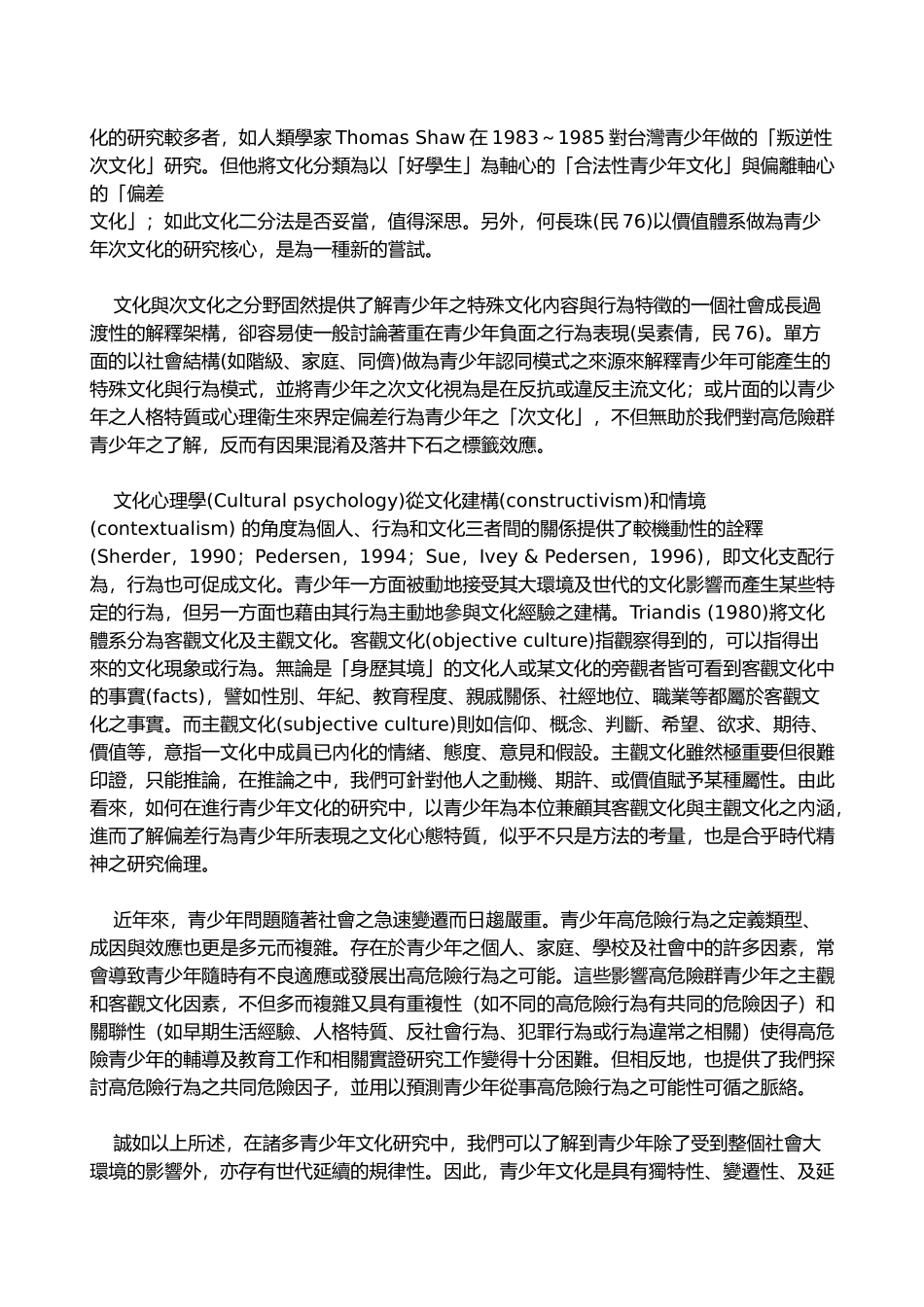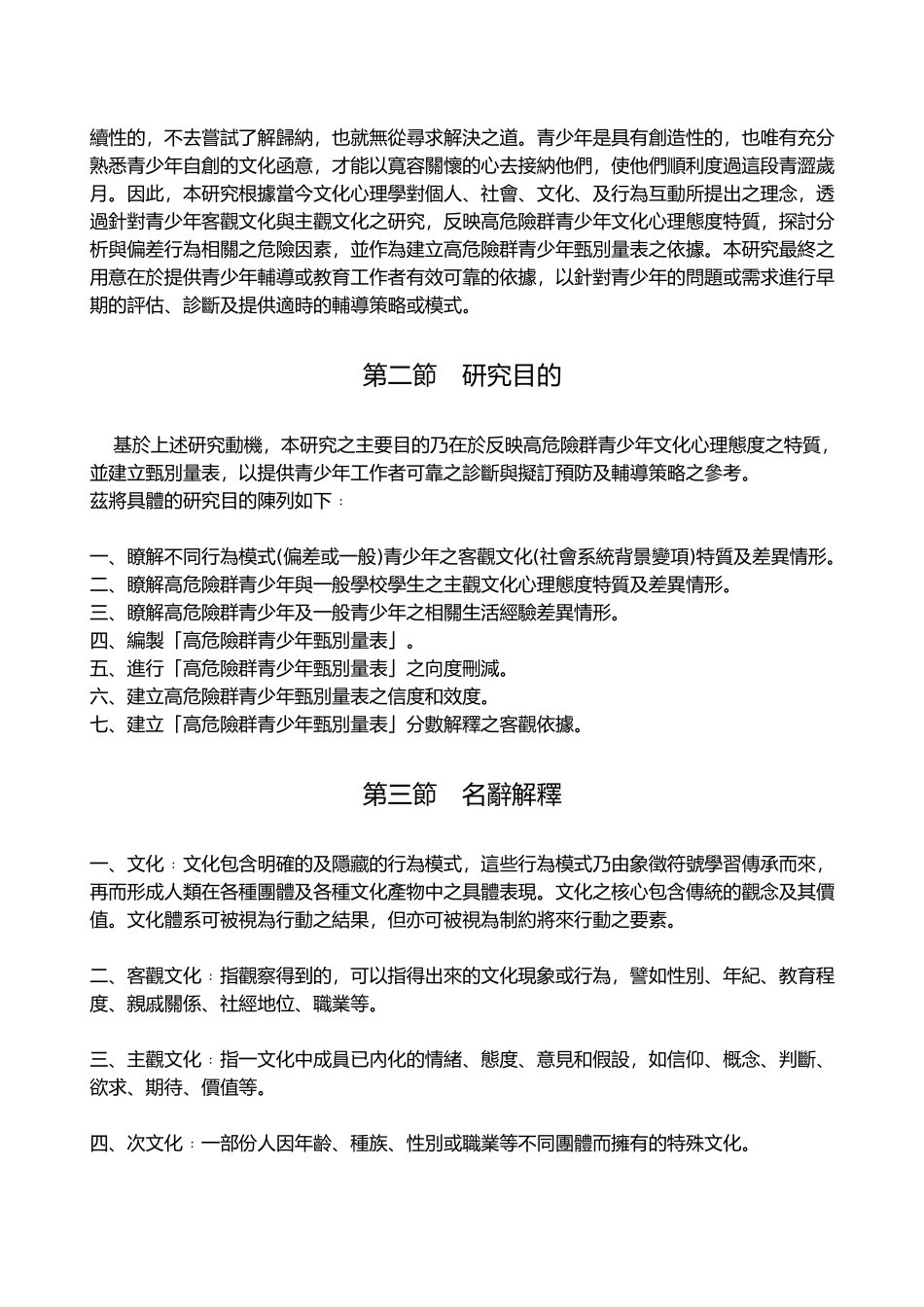高危險群青少年文化心態特質與甄別量表編製之研究第一章緒論第一節研究動機近年來,台灣的青少年問題隨著急速之社會經濟變遷、家庭結構改變與同儕影響而有日趨複雜化與嚴重化的傾向。青少年問題涵蓋面甚廣,從常見的偏差行為,如逃學、輟學、逃家、偷、賭、搶、恐嚇,到涉及更嚴重後果的未婚懷孕,濫用葯物、暴力、雛妓、自殺等,皆已對青少年身心發展、家庭功能、學校教育績效、及社會安寧構成相當程度之威脅與挑戰。以青少年犯罪為例,從近十年來犯罪人口分析,青少年犯罪人口始終佔總犯罪人口數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之間。再從犯罪趨勢來看,青少年犯罪之質與量日益惡化及犯罪年齡之降低,是不容否認的事實,(蔡德輝、楊士隆,民83)。教育部和許多地方教育機構已相繼推動多項因應性措施,如璞玉專案、朝陽方案、攜手計畫、春暉專案、認輔制度,自我傷害防制小組等,目的在於發展解決社會青少年問題之積極策略(教育部訓委會,民85)。各相關領域之青少年專家學者,也紛紛從輔導教育、心理、社會工作、犯罪學等專業角度來研究探討青少年文化心態(如黃正鵠、楊瑞珠,民85,系列報告一~十二),及研究青少年偏差行為之成因,並謀求相對之輔導策略。了解比較當代偏差行為經驗青少年和一般青少年文化心理態度之差異,有助於我們對影響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危險因素(riskfactors)之認識、分析與歸納。從輔導的角度來看,以下有兩個關於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問題亟待解答。第一個問題是,在同一群成長中的青少年裡,是什麼因素使某些青少年脫離所謂一般青少年的發展,漸漸形成一些社會無法接受的特質或行為表現,並因而在日後成為一個在家庭、學校及工作生活中無法正常運作的人?第二個問題是,如果我們能在青少年成長過程中察覺並掌握到一些早期的特殊癥兆,這是否意味著青少年問題確實可以預防,並可從輔導或教育的角度提昇增進其生活適應能力,以減低其經驗偏差行為或偏差行為後果的危險性?針對第一個問題而言,了解及比較當代有偏差行為經驗青少年及一般青少年的文化社會背景及個人心理態度之差異,有助於我們對影響青少年偏差行為之「危險因素」之認識、分析與歸納。針對第二個問題而言,我們可以依據這些危險因素進而辨識具有偏差行為傾向的「高危險群青少年」(At-riskadolescents),並據此發展及時而具體之青少年偏差行為之早期診斷與防治之諮商輔導策略。當今諸多探討青少年文化、次文化、心態或行為之研究乃因應社會變遷中之青少年問題而起。尤其以青少年偏差行為為出發點對青少年文化所做的探討和關懷容易採取類似「譴責」、「憂慮」之態度或聯想(余德慧,民84;吳素倩,民76)。到目前為止,在青少年文化的研究較多者,如人類學家ThomasShaw在1983~1985對台灣青少年做的「叛逆性次文化」研究。但他將文化分類為以「好學生」為軸心的「合法性青少年文化」與偏離軸心的「偏差文化」;如此文化二分法是否妥當,值得深思。另外,何長珠(民76)以價值體系做為青少年次文化的研究核心,是為一種新的嘗試。文化與次文化之分野固然提供了解青少年之特殊文化內容與行為特徵的一個社會成長過渡性的解釋架構,卻容易使一般討論著重在青少年負面之行為表現(吳素倩,民76)。單方面的以社會結構(如階級、家庭、同儕)做為青少年認同模式之來源來解釋青少年可能產生的特殊文化與行為模式,並將青少年之次文化視為是在反抗或違反主流文化;或片面的以青少年之人格特質或心理衛生來界定偏差行為青少年之「次文化」,不但無助於我們對高危險群青少年之了解,反而有因果混淆及落井下石之標籤效應。文化心理學(Culturalpsychology)從文化建構(constructivism)和情境(contextualism)的角度為個人、行為和文化三者間的關係提供了較機動性的詮釋(Sherder,1990;Pedersen,1994;Sue,Ivey&Pedersen,1996),即文化支配行為,行為也可促成文化。青少年一方面被動地接受其大環境及世代的文化影響而產生某些特定的行為,但另一方面也藉由其行為主動地參與文化經驗之建構。Triandis(1980)將文化體系分為客觀文化及主觀文化。客觀文化(objectiveculture)指觀察得到的,可以指得出來的文化現象或行為。無論是「身歷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