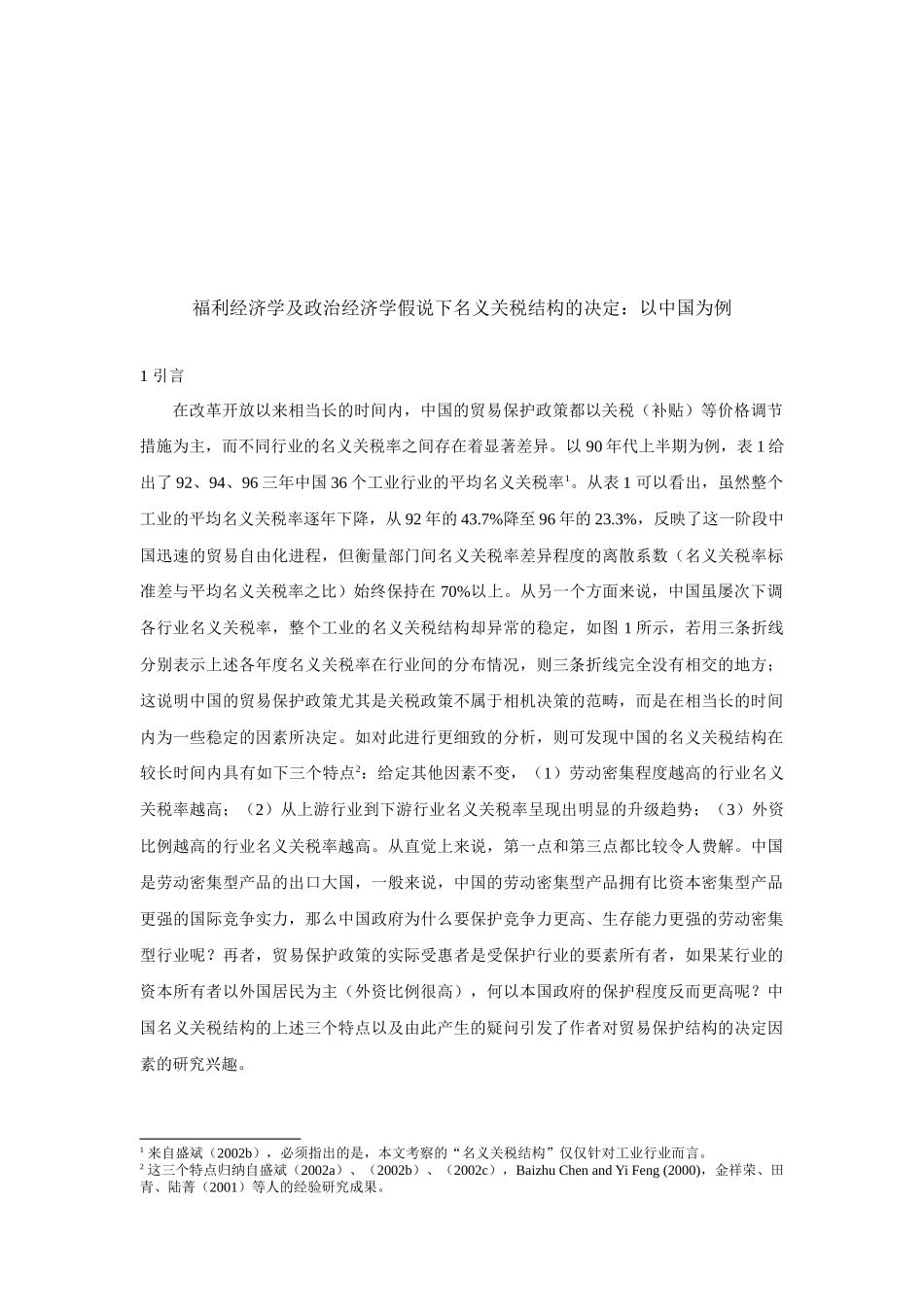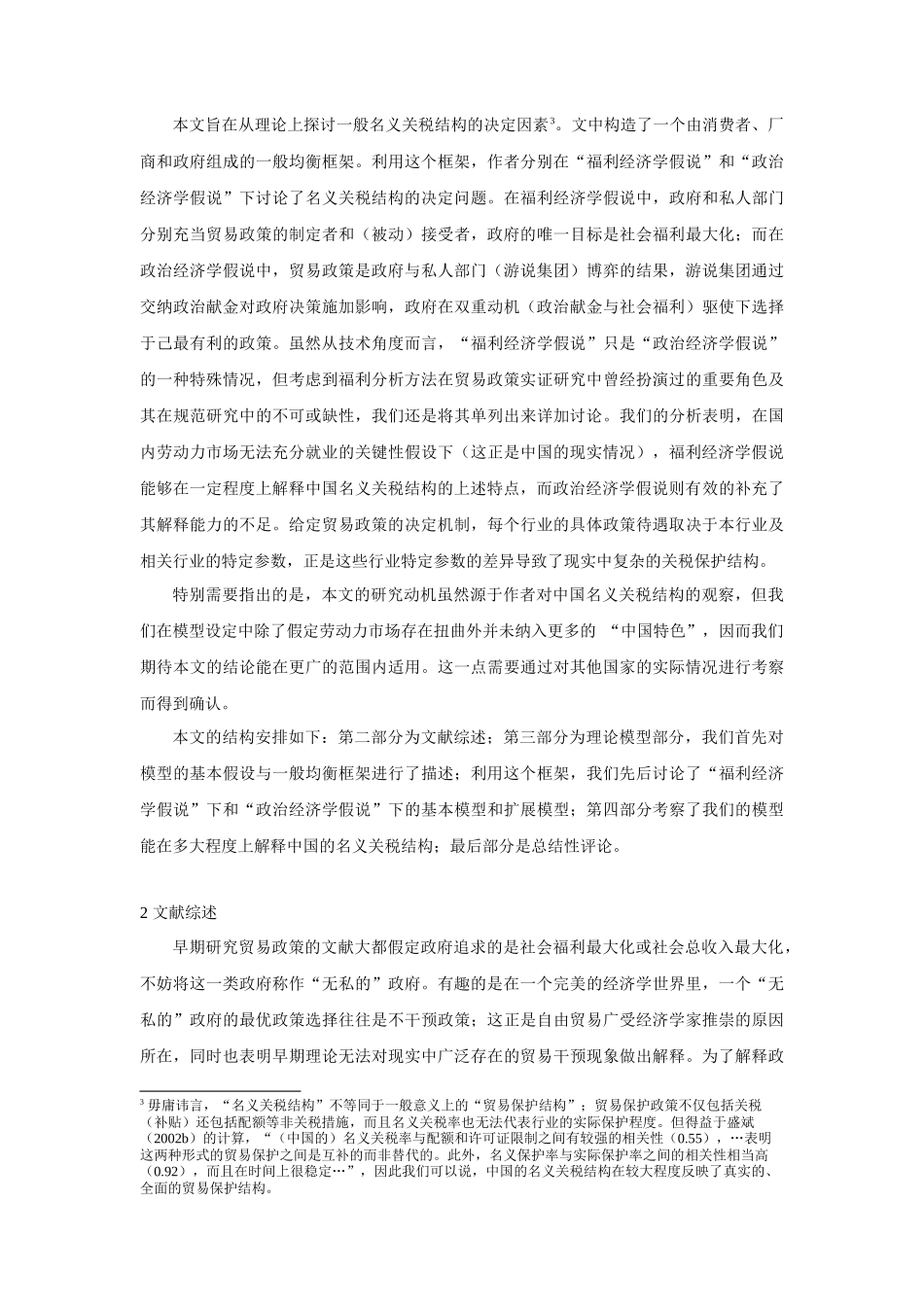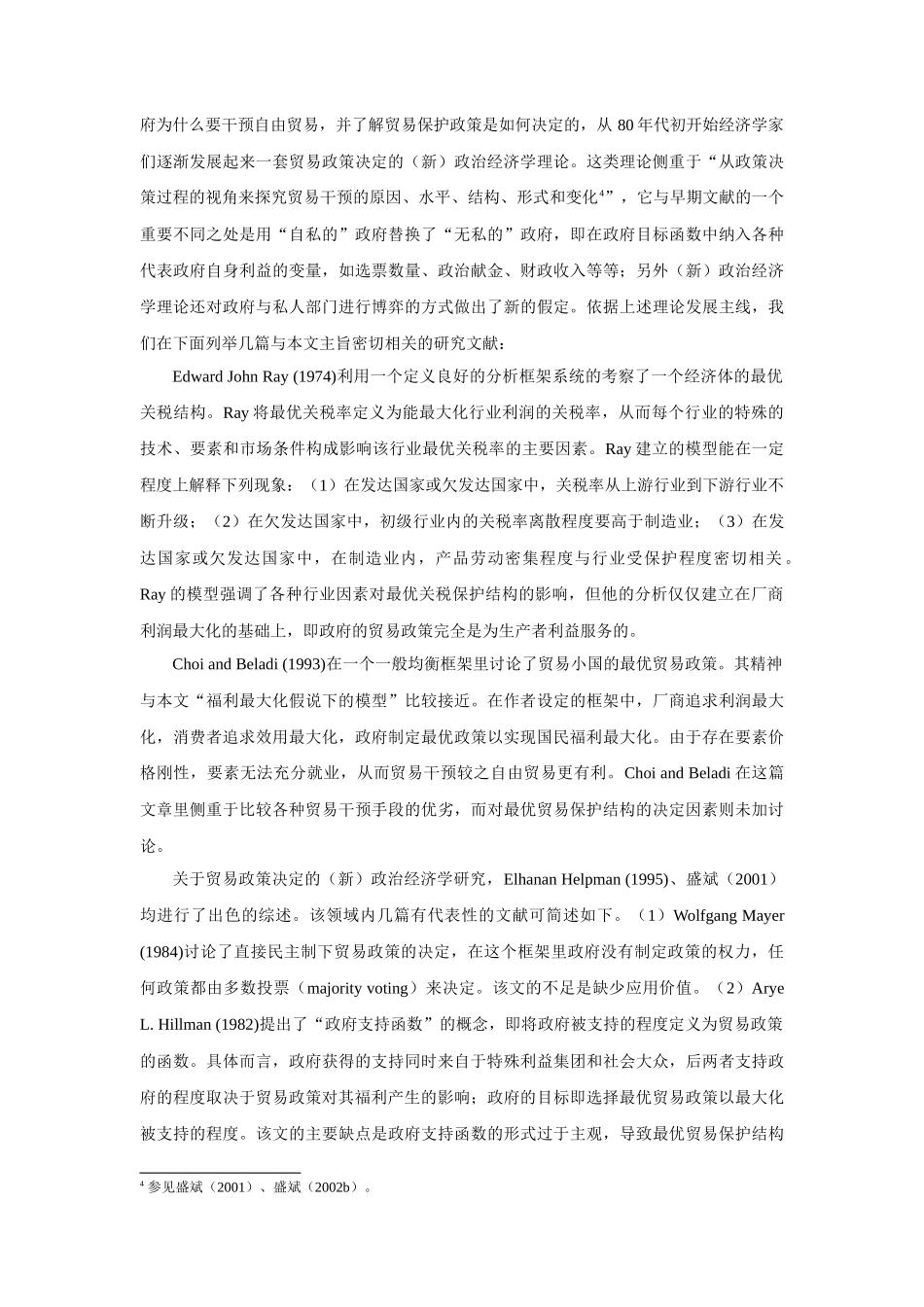福利经济学及政治经济学假说下名义关税结构的决定:以中国为例1引言在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贸易保护政策都以关税(补贴)等价格调节措施为主,而不同行业的名义关税率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以90年代上半期为例,表1给出了92、94、96三年中国36个工业行业的平均名义关税率1。从表1可以看出,虽然整个工业的平均名义关税率逐年下降,从92年的43.7%降至96年的23.3%,反映了这一阶段中国迅速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但衡量部门间名义关税率差异程度的离散系数(名义关税率标准差与平均名义关税率之比)始终保持在70%以上。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中国虽屡次下调各行业名义关税率,整个工业的名义关税结构却异常的稳定,如图1所示,若用三条折线分别表示上述各年度名义关税率在行业间的分布情况,则三条折线完全没有相交的地方;这说明中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尤其是关税政策不属于相机决策的范畴,而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一些稳定的因素所决定。如对此进行更细致的分析,则可发现中国的名义关税结构在较长时间内具有如下三个特点2:给定其他因素不变,(1)劳动密集程度越高的行业名义关税率越高;(2)从上游行业到下游行业名义关税率呈现出明显的升级趋势;(3)外资比例越高的行业名义关税率越高。从直觉上来说,第一点和第三点都比较令人费解。中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大国,一般来说,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拥有比资本密集型产品更强的国际竞争实力,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要保护竞争力更高、生存能力更强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呢?再者,贸易保护政策的实际受惠者是受保护行业的要素所有者,如果某行业的资本所有者以外国居民为主(外资比例很高),何以本国政府的保护程度反而更高呢?中国名义关税结构的上述三个特点以及由此产生的疑问引发了作者对贸易保护结构的决定因素的研究兴趣。1来自盛斌(2002b),必须指出的是,本文考察的“名义关税结构”仅仅针对工业行业而言。2这三个特点归纳自盛斌(2002a)、(2002b)、(2002c),BaizhuChenandYiFeng(2000),金祥荣、田青、陆菁(2001)等人的经验研究成果。本文旨在从理论上探讨一般名义关税结构的决定因素3。文中构造了一个由消费者、厂商和政府组成的一般均衡框架。利用这个框架,作者分别在“福利经济学假说”和“政治经济学假说”下讨论了名义关税结构的决定问题。在福利经济学假说中,政府和私人部门分别充当贸易政策的制定者和(被动)接受者,政府的唯一目标是社会福利最大化;而在政治经济学假说中,贸易政策是政府与私人部门(游说集团)博弈的结果,游说集团通过交纳政治献金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政府在双重动机(政治献金与社会福利)驱使下选择于己最有利的政策。虽然从技术角度而言,“福利经济学假说”只是“政治经济学假说”的一种特殊情况,但考虑到福利分析方法在贸易政策实证研究中曾经扮演过的重要角色及其在规范研究中的不可或缺性,我们还是将其单列出来详加讨论。我们的分析表明,在国内劳动力市场无法充分就业的关键性假设下(这正是中国的现实情况),福利经济学假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名义关税结构的上述特点,而政治经济学假说则有效的补充了其解释能力的不足。给定贸易政策的决定机制,每个行业的具体政策待遇取决于本行业及相关行业的特定参数,正是这些行业特定参数的差异导致了现实中复杂的关税保护结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研究动机虽然源于作者对中国名义关税结构的观察,但我们在模型设定中除了假定劳动力市场存在扭曲外并未纳入更多的“中国特色”,因而我们期待本文的结论能在更广的范围内适用。这一点需要通过对其他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考察而得到确认。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为理论模型部分,我们首先对模型的基本假设与一般均衡框架进行了描述;利用这个框架,我们先后讨论了“福利经济学假说”下和“政治经济学假说”下的基本模型和扩展模型;第四部分考察了我们的模型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中国的名义关税结构;最后部分是总结性评论。2文献综述早期研究贸易政策的文献大都假定政府追求的是社会福利最大化或社会总收入最大化,不妨将这一类政府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