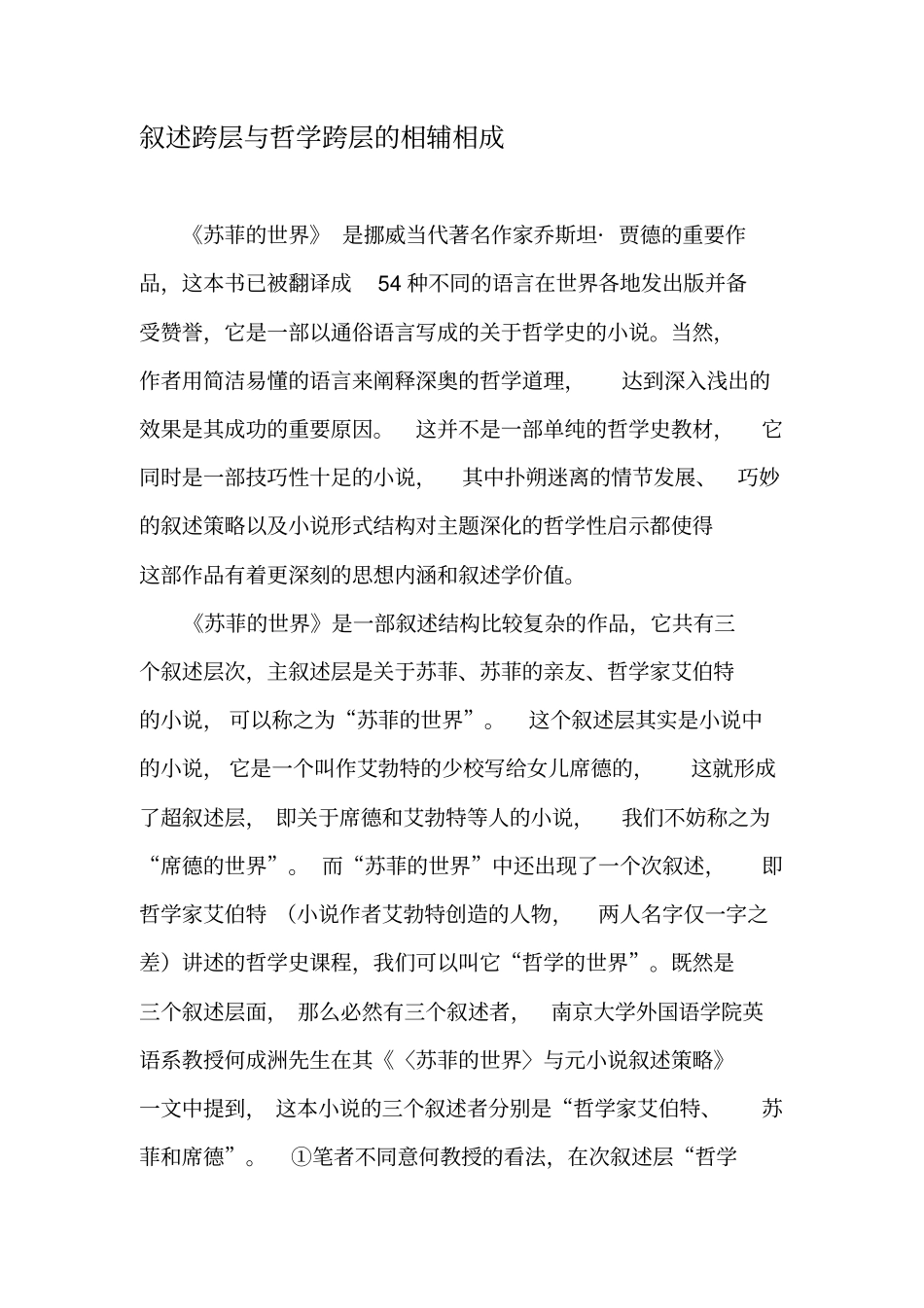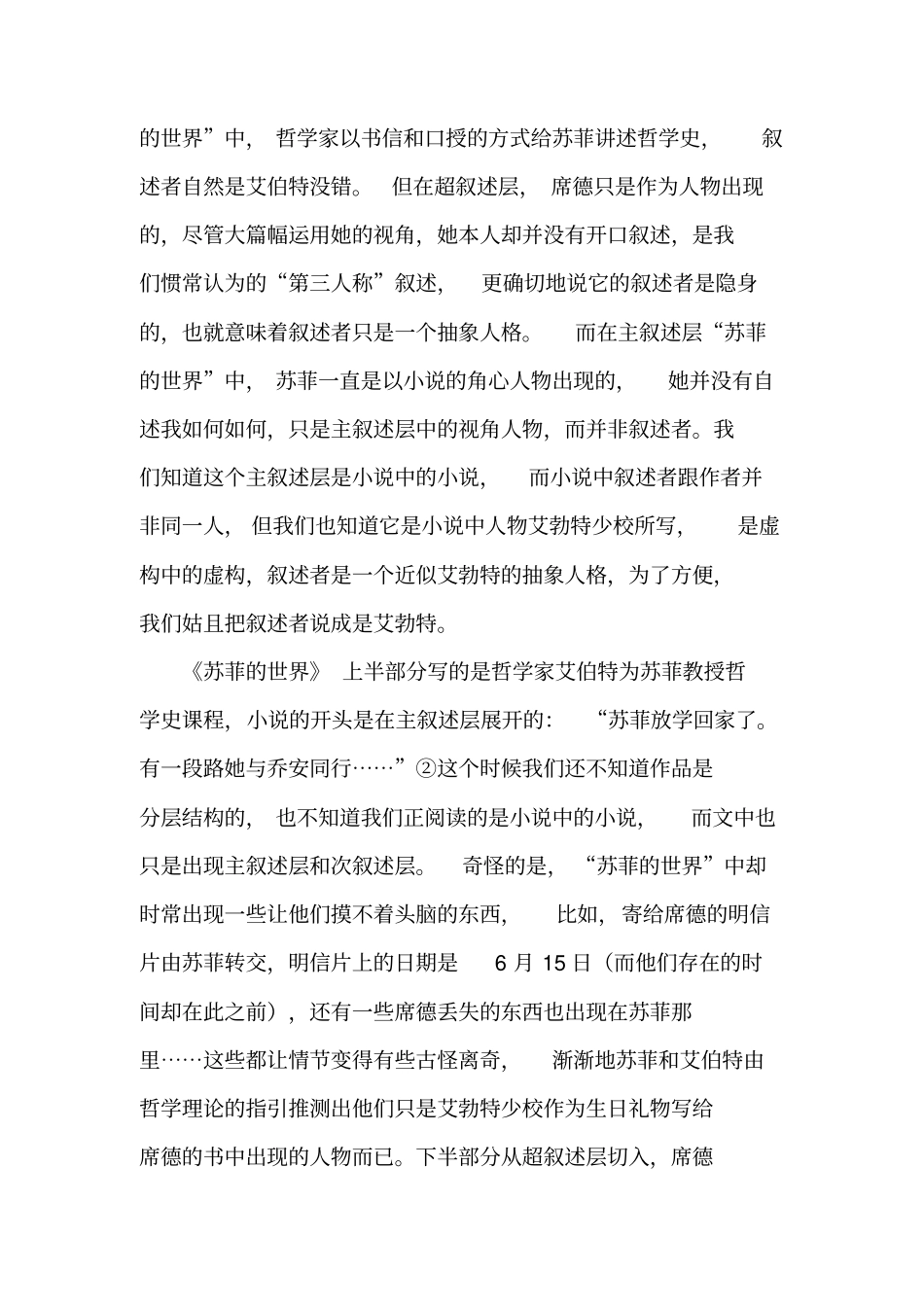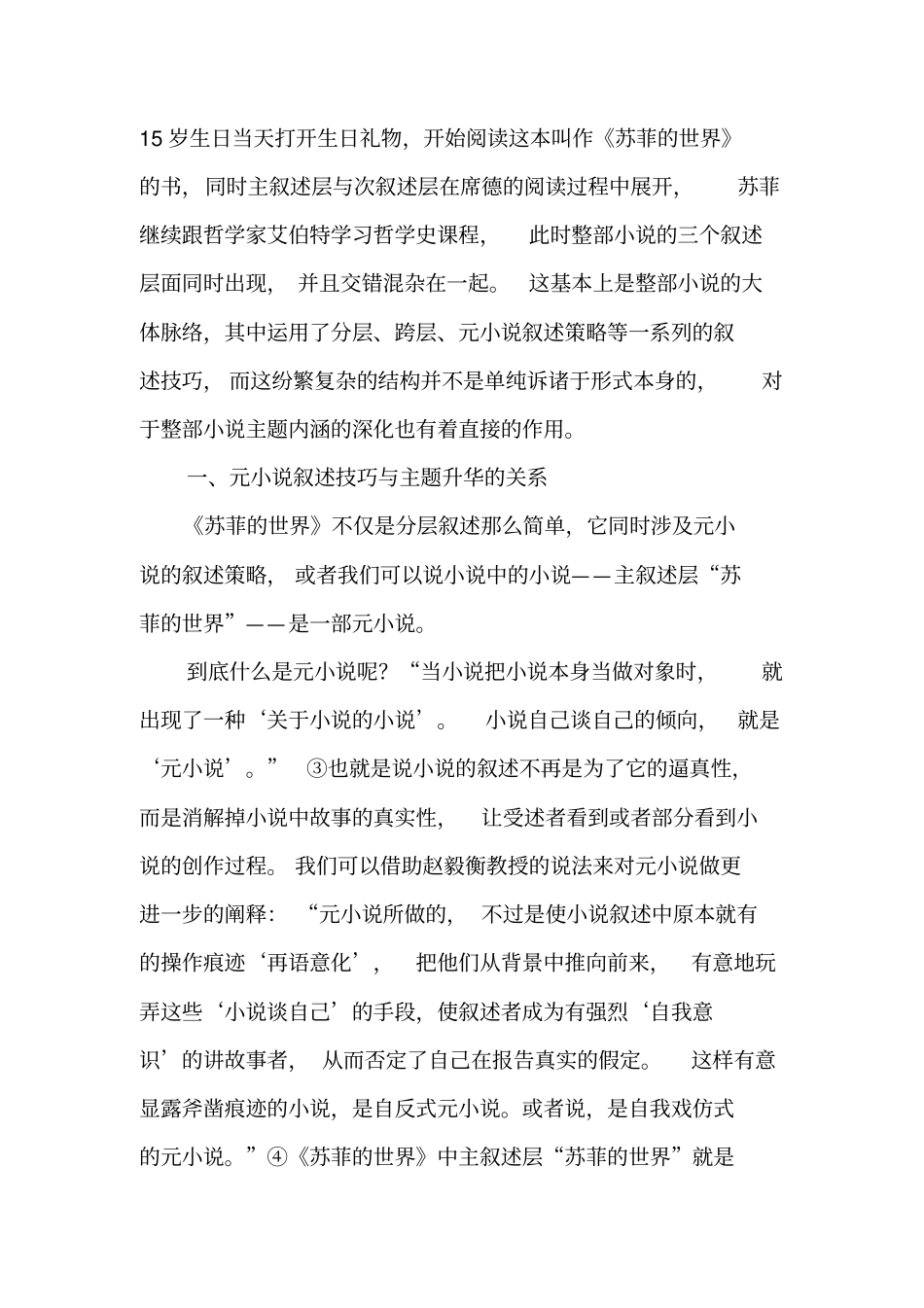叙述跨层与哲学跨层的相辅相成《苏菲的世界》是挪威当代著名作家乔斯坦·贾德的重要作品,这本书已被翻译成54种不同的语言在世界各地发出版并备受赞誉,它是一部以通俗语言写成的关于哲学史的小说。当然,作者用简洁易懂的语言来阐释深奥的哲学道理,达到深入浅出的效果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这并不是一部单纯的哲学史教材,它同时是一部技巧性十足的小说,其中扑朔迷离的情节发展、巧妙的叙述策略以及小说形式结构对主题深化的哲学性启示都使得这部作品有着更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叙述学价值。《苏菲的世界》是一部叙述结构比较复杂的作品,它共有三个叙述层次,主叙述层是关于苏菲、苏菲的亲友、哲学家艾伯特的小说,可以称之为“苏菲的世界”。这个叙述层其实是小说中的小说,它是一个叫作艾勃特的少校写给女儿席德的,这就形成了超叙述层,即关于席德和艾勃特等人的小说,我们不妨称之为“席德的世界”。而“苏菲的世界”中还出现了一个次叙述,即哲学家艾伯特(小说作者艾勃特创造的人物,两人名字仅一字之差)讲述的哲学史课程,我们可以叫它“哲学的世界”。既然是三个叙述层面,那么必然有三个叙述者,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何成洲先生在其《〈苏菲的世界〉与元小说叙述策略》一文中提到,这本小说的三个叙述者分别是“哲学家艾伯特、苏菲和席德”。①笔者不同意何教授的看法,在次叙述层“哲学的世界”中,哲学家以书信和口授的方式给苏菲讲述哲学史,叙述者自然是艾伯特没错。但在超叙述层,席德只是作为人物出现的,尽管大篇幅运用她的视角,她本人却并没有开口叙述,是我们惯常认为的“第三人称”叙述,更确切地说它的叙述者是隐身的,也就意味着叙述者只是一个抽象人格。而在主叙述层“苏菲的世界”中,苏菲一直是以小说的角心人物出现的,她并没有自述我如何如何,只是主叙述层中的视角人物,而并非叙述者。我们知道这个主叙述层是小说中的小说,而小说中叙述者跟作者并非同一人,但我们也知道它是小说中人物艾勃特少校所写,是虚构中的虚构,叙述者是一个近似艾勃特的抽象人格,为了方便,我们姑且把叙述者说成是艾勃特。《苏菲的世界》上半部分写的是哲学家艾伯特为苏菲教授哲学史课程,小说的开头是在主叙述层展开的:“苏菲放学回家了。有一段路她与乔安同行⋯⋯”②这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作品是分层结构的,也不知道我们正阅读的是小说中的小说,而文中也只是出现主叙述层和次叙述层。奇怪的是,“苏菲的世界”中却时常出现一些让他们摸不着头脑的东西,比如,寄给席德的明信片由苏菲转交,明信片上的日期是6月15日(而他们存在的时间却在此之前),还有一些席德丢失的东西也出现在苏菲那里⋯⋯这些都让情节变得有些古怪离奇,渐渐地苏菲和艾伯特由哲学理论的指引推测出他们只是艾勃特少校作为生日礼物写给席德的书中出现的人物而已。下半部分从超叙述层切入,席德15岁生日当天打开生日礼物,开始阅读这本叫作《苏菲的世界》的书,同时主叙述层与次叙述层在席德的阅读过程中展开,苏菲继续跟哲学家艾伯特学习哲学史课程,此时整部小说的三个叙述层面同时出现,并且交错混杂在一起。这基本上是整部小说的大体脉络,其中运用了分层、跨层、元小说叙述策略等一系列的叙述技巧,而这纷繁复杂的结构并不是单纯诉诸于形式本身的,对于整部小说主题内涵的深化也有着直接的作用。一、元小说叙述技巧与主题升华的关系《苏菲的世界》不仅是分层叙述那么简单,它同时涉及元小说的叙述策略,或者我们可以说小说中的小说——主叙述层“苏菲的世界”——是一部元小说。到底什么是元小说呢?“当小说把小说本身当做对象时,就出现了一种‘关于小说的小说’。小说自己谈自己的倾向,就是‘元小说’。”③也就是说小说的叙述不再是为了它的逼真性,而是消解掉小说中故事的真实性,让受述者看到或者部分看到小说的创作过程。我们可以借助赵毅衡教授的说法来对元小说做更进一步的阐释:“元小说所做的,不过是使小说叙述中原本就有的操作痕迹‘再语意化’,把他们从背景中推向前来,有意地玩弄这些‘小说谈自己’的手段,使叙述者成为有强烈‘自我意识’的讲故事者,从而否定了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