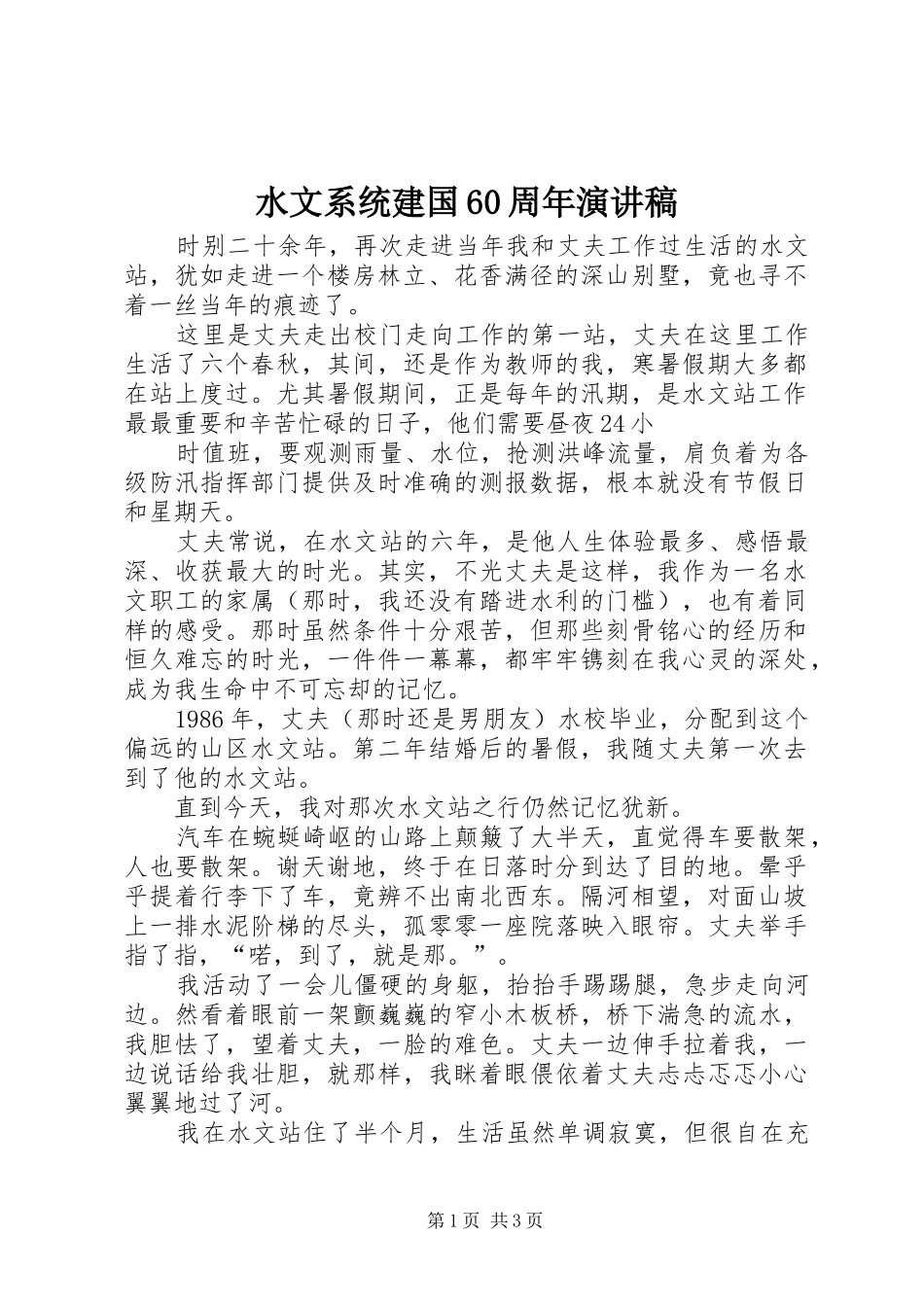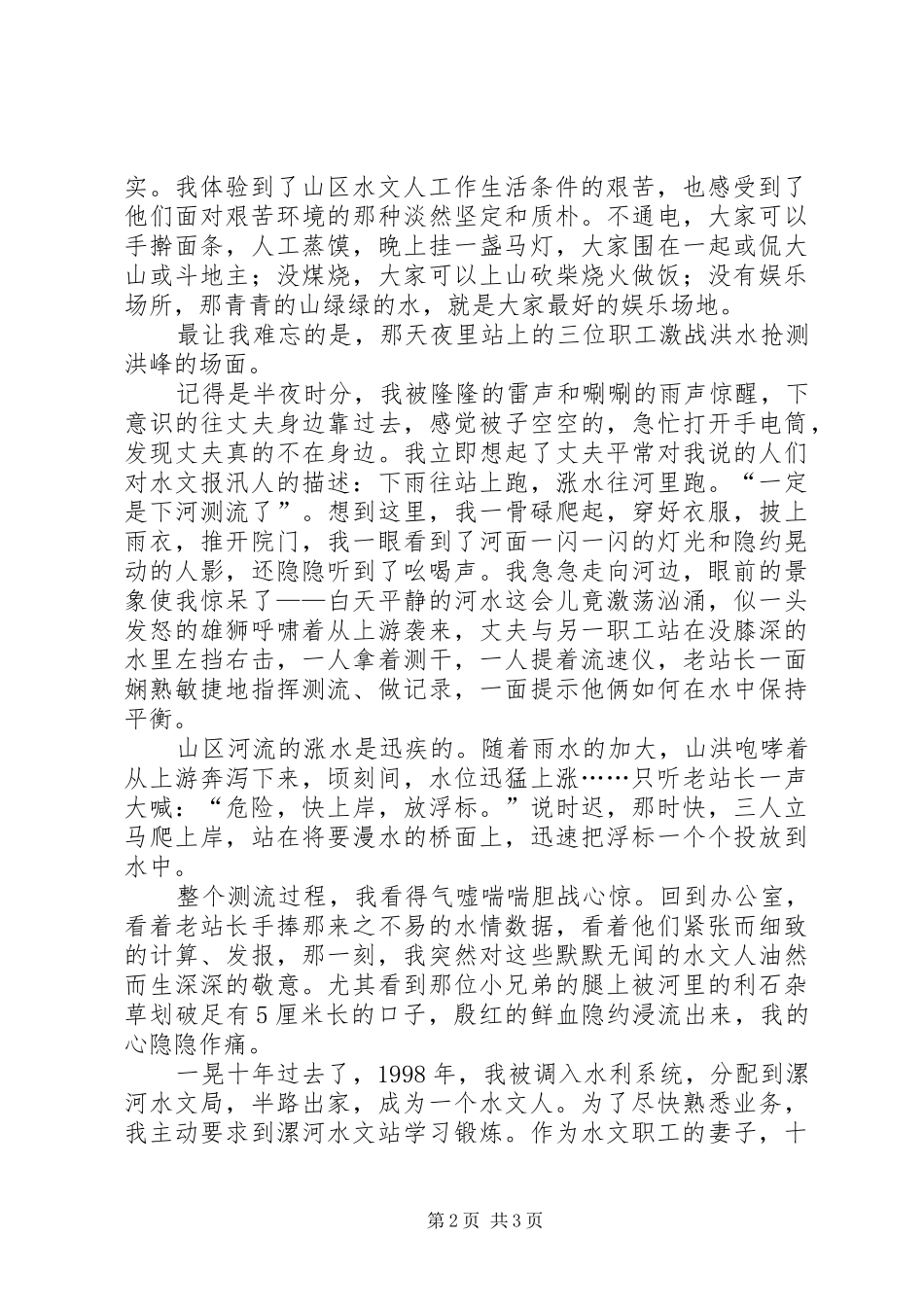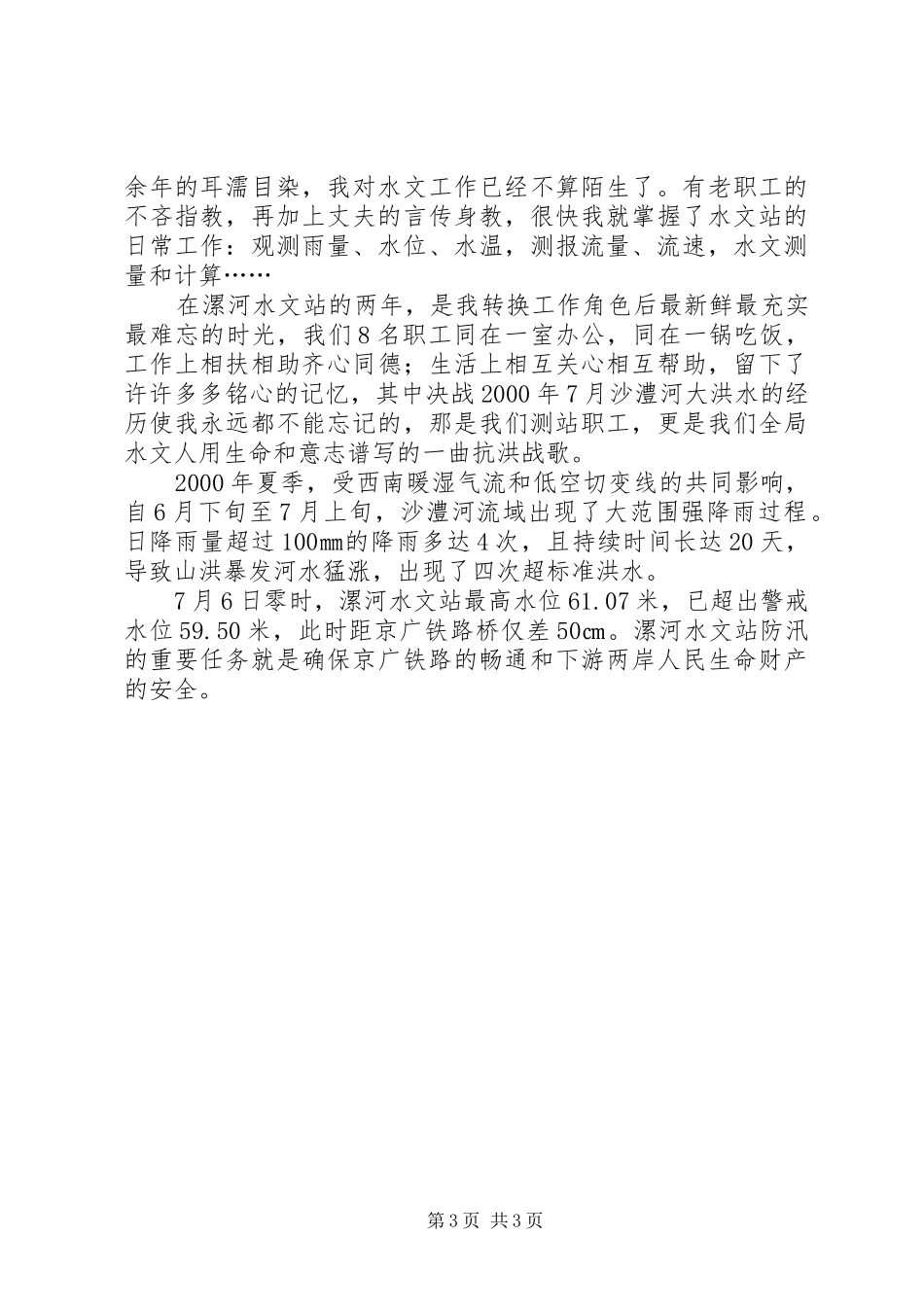水文系统建国60周年演讲稿时别二十余年,再次走进当年我和丈夫工作过生活的水文站,犹如走进一个楼房林立、花香满径的深山别墅,竟也寻不着一丝当年的痕迹了。这里是丈夫走出校门走向工作的第一站,丈夫在这里工作生活了六个春秋,其间,还是作为教师的我,寒暑假期大多都在站上度过。尤其暑假期间,正是每年的汛期,是水文站工作最最重要和辛苦忙碌的日子,他们需要昼夜24小时值班,要观测雨量、水位,抢测洪峰流量,肩负着为各级防汛指挥部门提供及时准确的测报数据,根本就没有节假日和星期天。丈夫常说,在水文站的六年,是他人生体验最多、感悟最深、收获最大的时光。其实,不光丈夫是这样,我作为一名水文职工的家属(那时,我还没有踏进水利的门槛),也有着同样的感受。那时虽然条件十分艰苦,但那些刻骨铭心的经历和恒久难忘的时光,一件件一幕幕,都牢牢镌刻在我心灵的深处,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忘却的记忆。1986年,丈夫(那时还是男朋友)水校毕业,分配到这个偏远的山区水文站。第二年结婚后的暑假,我随丈夫第一次去到了他的水文站。直到今天,我对那次水文站之行仍然记忆犹新。汽车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了大半天,直觉得车要散架,人也要散架。谢天谢地,终于在日落时分到达了目的地。晕乎乎提着行李下了车,竟辨不出南北西东。隔河相望,对面山坡上一排水泥阶梯的尽头,孤零零一座院落映入眼帘。丈夫举手指了指,“喏,到了,就是那。”。我活动了一会儿僵硬的身躯,抬抬手踢踢腿,急步走向河边。然看着眼前一架颤巍巍的窄小木板桥,桥下湍急的流水,我胆怯了,望着丈夫,一脸的难色。丈夫一边伸手拉着我,一边说话给我壮胆,就那样,我眯着眼偎依着丈夫忐忐忑忑小心翼翼地过了河。我在水文站住了半个月,生活虽然单调寂寞,但很自在充第1页共3页实。我体验到了山区水文人工作生活条件的艰苦,也感受到了他们面对艰苦环境的那种淡然坚定和质朴。不通电,大家可以手擀面条,人工蒸馍,晚上挂一盏马灯,大家围在一起或侃大山或斗地主;没煤烧,大家可以上山砍柴烧火做饭;没有娱乐场所,那青青的山绿绿的水,就是大家最好的娱乐场地。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天夜里站上的三位职工激战洪水抢测洪峰的场面。记得是半夜时分,我被隆隆的雷声和唰唰的雨声惊醒,下意识的往丈夫身边靠过去,感觉被子空空的,急忙打开手电筒,发现丈夫真的不在身边。我立即想起了丈夫平常对我说的人们对水文报汛人的描述:下雨往站上跑,涨水往河里跑。“一定是下河测流了”。想到这里,我一骨碌爬起,穿好衣服,披上雨衣,推开院门,我一眼看到了河面一闪一闪的灯光和隐约晃动的人影,还隐隐听到了吆喝声。我急急走向河边,眼前的景象使我惊呆了——白天平静的河水这会儿竟激荡汹涌,似一头发怒的雄狮呼啸着从上游袭来,丈夫与另一职工站在没膝深的水里左挡右击,一人拿着测干,一人提着流速仪,老站长一面娴熟敏捷地指挥测流、做记录,一面提示他俩如何在水中保持平衡。山区河流的涨水是迅疾的。随着雨水的加大,山洪咆哮着从上游奔泻下来,顷刻间,水位迅猛上涨……只听老站长一声大喊:“危险,快上岸,放浮标。”说时迟,那时快,三人立马爬上岸,站在将要漫水的桥面上,迅速把浮标一个个投放到水中。整个测流过程,我看得气嘘喘喘胆战心惊。回到办公室,看着老站长手捧那来之不易的水情数据,看着他们紧张而细致的计算、发报,那一刻,我突然对这些默默无闻的水文人油然而生深深的敬意。尤其看到那位小兄弟的腿上被河里的利石杂草划破足有5厘米长的口子,殷红的鲜血隐约浸流出来,我的心隐隐作痛。一晃十年过去了,1998年,我被调入水利系统,分配到漯河水文局,半路出家,成为一个水文人。为了尽快熟悉业务,我主动要求到漯河水文站学习锻炼。作为水文职工的妻子,十第2页共3页余年的耳濡目染,我对水文工作已经不算陌生了。有老职工的不吝指教,再加上丈夫的言传身教,很快我就掌握了水文站的日常工作:观测雨量、水位、水温,测报流量、流速,水文测量和计算……在漯河水文站的两年,是我转换工作角色后最新鲜最充实最难忘的时光,我们8名职工同在一室办公,同在一锅吃饭,工作上相扶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