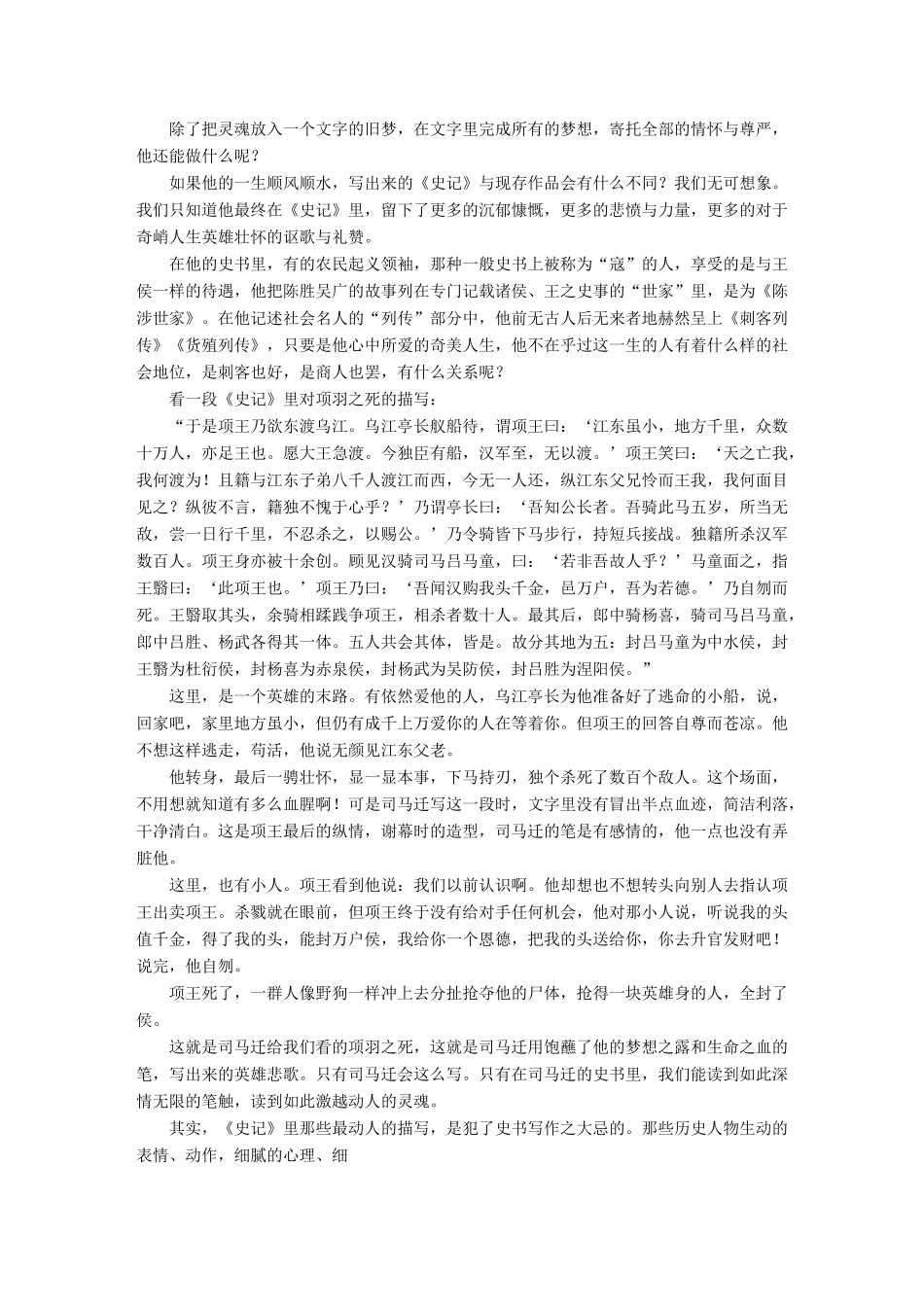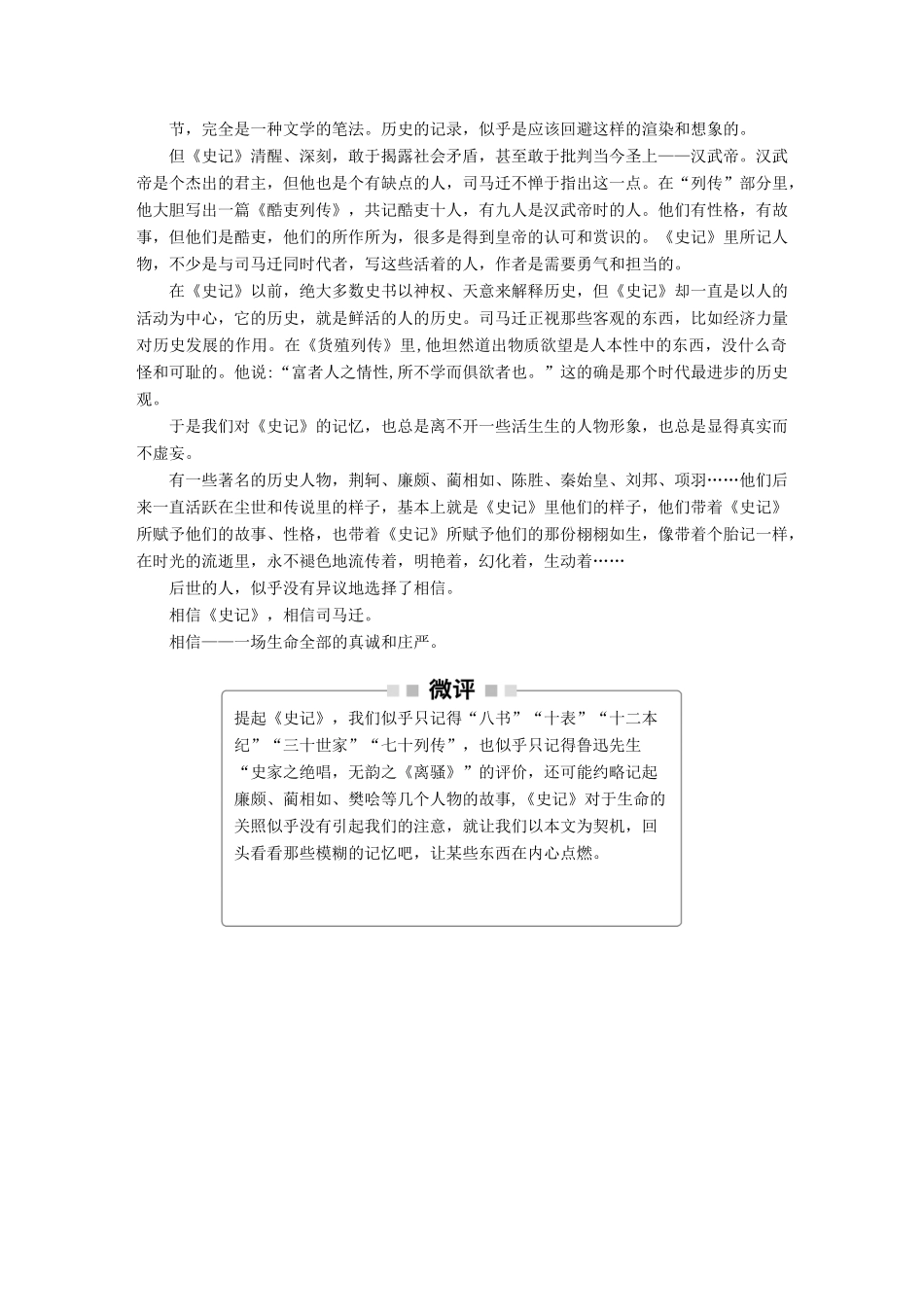周3品美文吟一句无韵之《离骚》,浅浅地亲近《史记》关于《史记》,鲁迅的那句评价,似乎比它文本中的所有原句都有名:“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很像传说,见不到主角,只听见传说。《离骚》,现在的人读起来是很艰难的。周杰伦唱一曲《菊花台》,如诗如谜,意象模糊,但大家一听就能全盘感受那种流行的美丽味道。而感觉《离骚》之美,就无比艰涩,一点也不通畅。岁月横亘其间,生成了无比自然而巨大的障碍。我读书时,老师曾要求我们背诵《离骚》。老师的要求很节制,只要求我们背诵第一段。而如今,我只记得第一句了:“帝高阳之苗裔兮……”它的含义,也需要注解。无韵之《离骚》,也是一样。有多少人通读过《史记》呢?你没有,我也没有。又有多少人能无碍地阅读《史记》的语言?那份遥远的辉煌,已注定离我们越来越远,一般人再不可能和它有更深的缘分。只能,偶尔却又无可回避地,被它远而巨大的光芒晃一下眼睛;偶尔却也受惊般地,闻到一丝它深藏于久远年代的浓郁幽香的气息。像树荫间漏下的点点春阳。学生的课本里,会有它流芳百世的几个片断:完璧归赵、负荆请罪、鸿门宴、垓下之围……包括陈胜的那一句慷慨: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也包括荆轲刺秦前的那一曲回肠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我们借助浩淼的注解,感受其间的千古波澜,惊心动魄。也许这样浅浅的亲近就很好,已足够。一个叫司马迁的人,以一部巨著,完成了他生命的梦想与狂欢。而在流年里,渐渐地,以一种越发清淡的方式,给无数人一些朦胧而奇特的心灵恩泽。由此,有人发现谋略,有人思索人格,有人感叹爱情。司马迁想写《史记》的志向年轻时就有了,因为他父亲司马谈是个史官,写一部伟大的史书是父亲的夙愿,临终前,父亲把这个夙愿作为遗嘱交给了儿子司马迁。收下了父亲的嘱托,早年的司马迁,年少气盛,自负才华,又本能地对那些奇人奇事、英雄情怀入迷。他搜集素材,磨砺学问,一部巨著的幻影,朦朦胧胧地在远方召唤。但真正地把全部生命投入到《史记》的写作中去,是司马迁在遭受了宫刑以后的事了。所谓宫刑,就是把一个男人变作太监一样。受了宫刑的司马迁,不仅是个罪人,也是个不完整不健全的男人了。这是一场无妄之灾。汉武帝时名将李陵因兵败被俘投降了匈奴,司马迁和李陵并不熟,只是看不过有些人对李陵的过分辱没,看不过那种墙倒众人推把一个人曾经的好处也全部踩烂的世态,并且他认为李陵投降也自有他的苦衷,就荡然为他辩解了几句。这样他就让汉武帝不高兴了。让汉武帝这样的皇帝不高兴的后果是严重的。皇帝给了司马迁一个处罚:宫刑。然后,宫刑受了,司马迁没死。这样的司马迁,除了苟延残喘的肉体,除了像狗一样卑贱的日子,还有什么?还能怎样去活?去活得像一个人,甚至像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男儿呢?只有一部《史记》了。除了把灵魂放入一个文字的旧梦,在文字里完成所有的梦想,寄托全部的情怀与尊严,他还能做什么呢?如果他的一生顺风顺水,写出来的《史记》与现存作品会有什么不同?我们无可想象。我们只知道他最终在《史记》里,留下了更多的沉郁慷慨,更多的悲愤与力量,更多的对于奇峭人生英雄壮怀的讴歌与礼赞。在他的史书里,有的农民起义领袖,那种一般史书上被称为“寇”的人,享受的是与王侯一样的待遇,他把陈胜吴广的故事列在专门记载诸侯、王之史事的“世家”里,是为《陈涉世家》。在他记述社会名人的“列传”部分中,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赫然呈上《刺客列传》《货殖列传》,只要是他心中所爱的奇美人生,他不在乎过这一生的人有着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是刺客也好,是商人也罢,有什么关系呢?看一段《史记》里对项羽之死的描写:“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