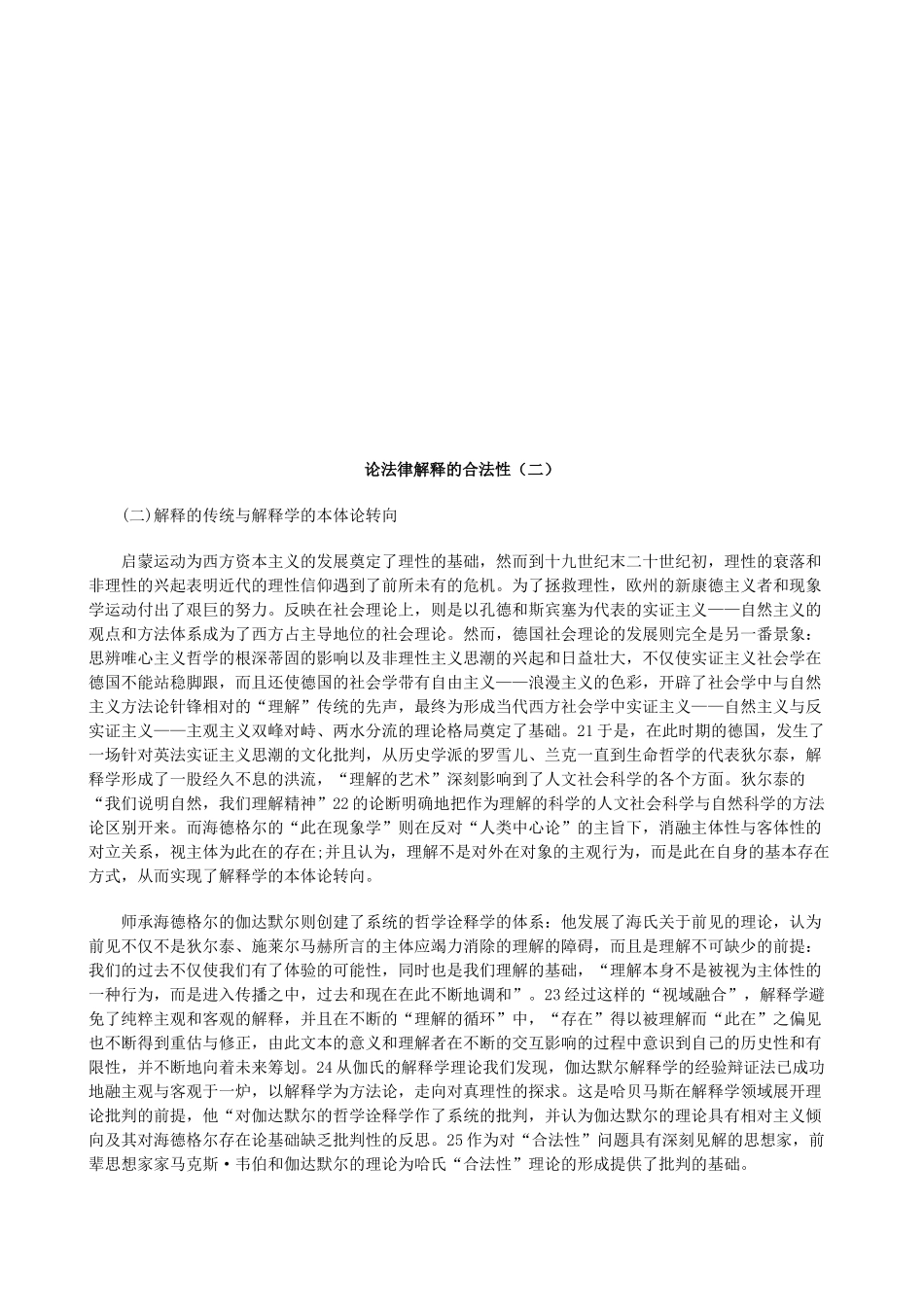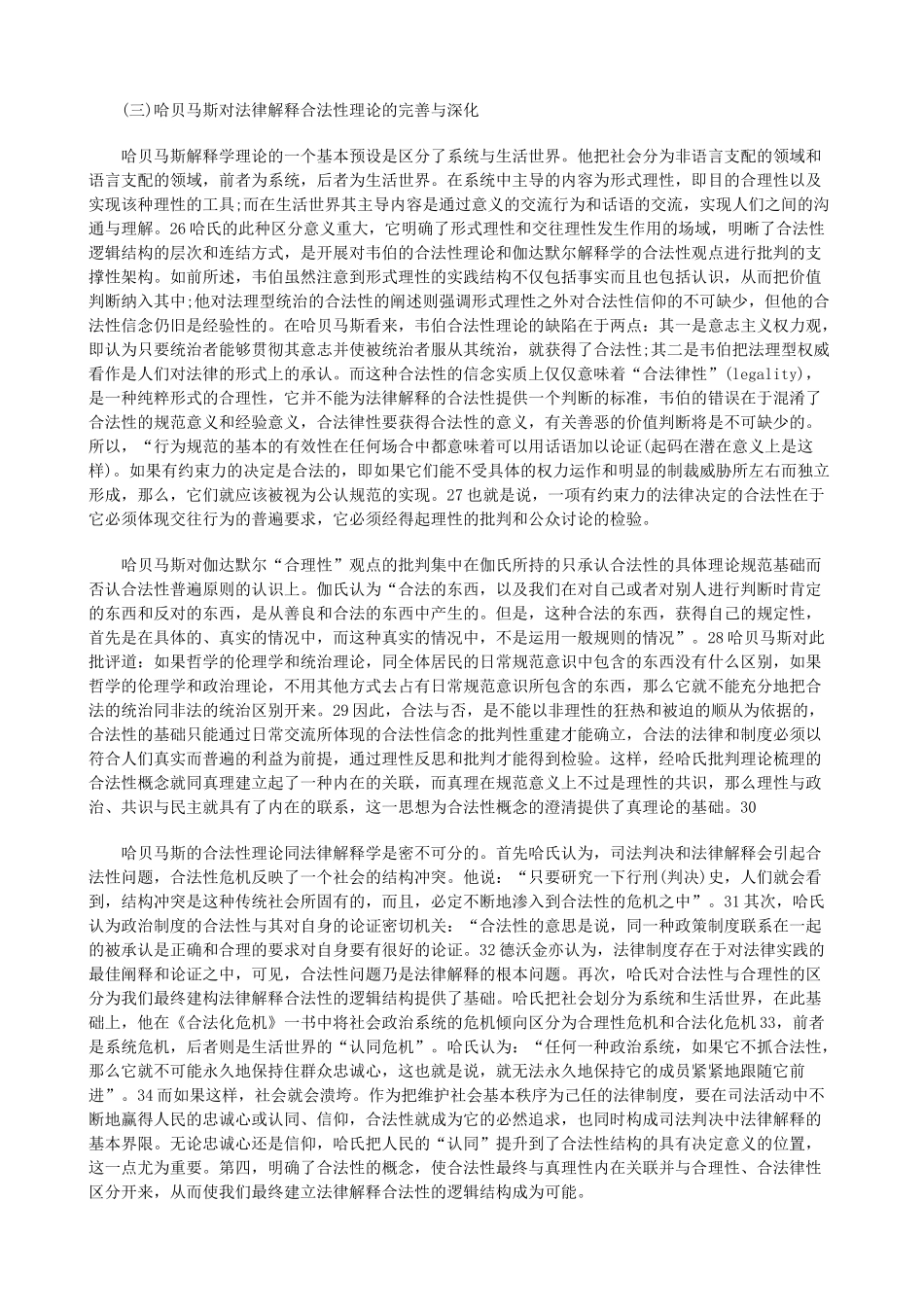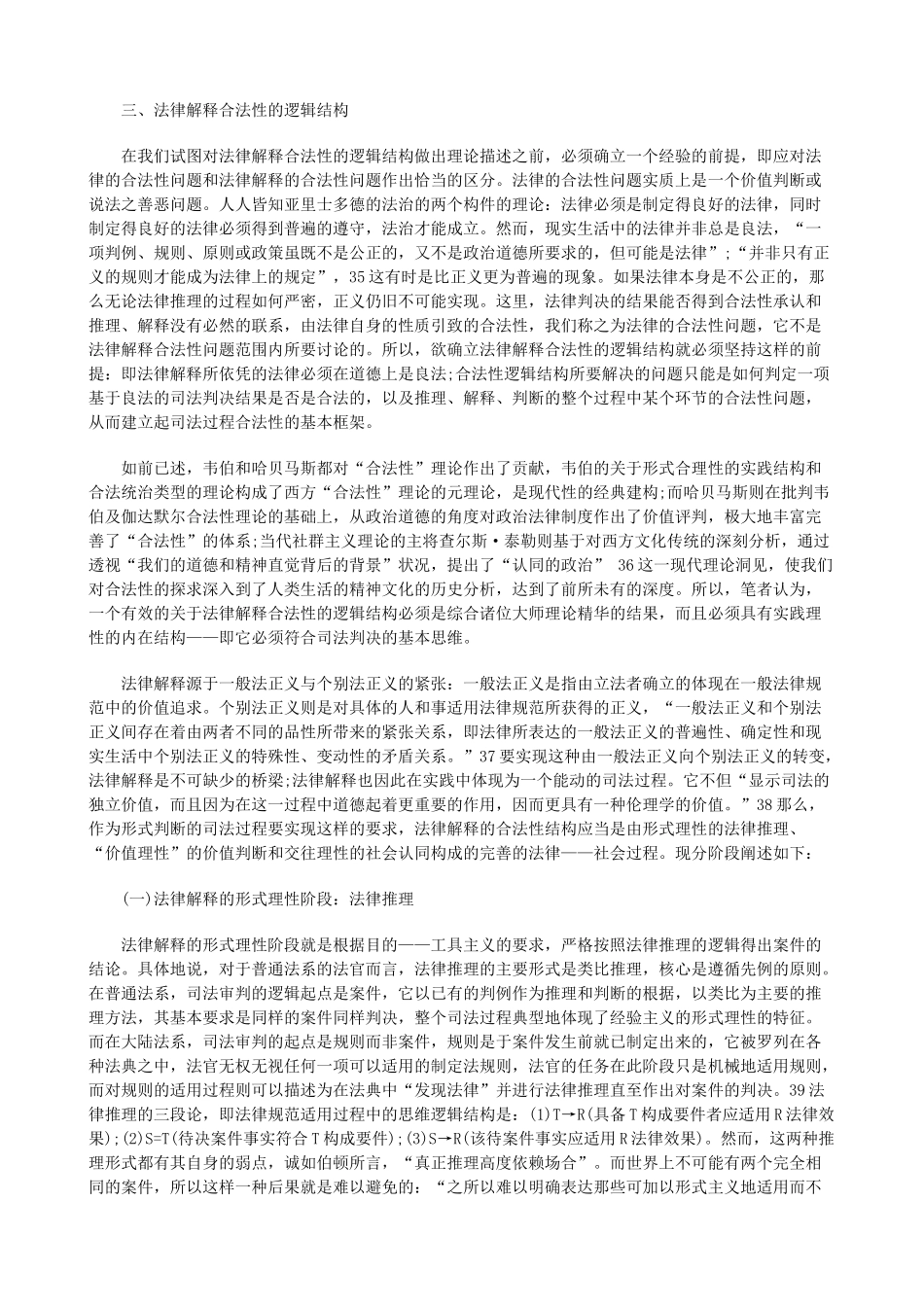A thesis submitted toXXX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for the degree ofMaster of Engineering论法律解释的合法性(二) (二)解释的传统与解释学的本体论转向 启蒙运动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理性的基础,然而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理性的衰落和非理性的兴起表明近代的理性信仰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为了拯救理性,欧州的新康德主义者和现象学运动付出了艰巨的努力。反映在社会理论上,则是以孔德和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自然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体系成为了西方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理论。然而,德国社会理论的发展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思辨唯心主义哲学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以及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和日益壮大,不仅使实证主义社会学在德国不能站稳脚跟,而且还使德国的社会学带有自由主义——浪漫主义的色彩,开辟了社会学中与自然主义方法论针锋相对的“理解”传统的先声,最终为形成当代西方社会学中实证主义——自然主义与反实证主义——主观主义双峰对峙、两水分流的理论格局奠定了基础。21 于是,在此时期的德国,发生了一场针对英法实证主义思潮的文化批判,从历史学派的罗雪儿、兰克一直到生命哲学的代表狄尔泰,解释学形成了一股经久不息的洪流,“理解的艺术”深刻影响到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狄尔泰的“我们说明自然,我们理解精神”22 的论断明确地把作为理解的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区别开来。而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则在反对“人类中心论”的主旨下,消融主体性与客体性的对立关系,视主体为此在的存在;并且认为,理解不是对外在对象的主观行为,而是此在自身的基本存在方式,从而实现了解释学的本体论转向。 师承海德格尔的伽达默尔则创建了系统的哲学诠释学的体系:他发展了海氏关于前见的理论,认为前见不仅不是狄尔泰、施莱尔马赫所言的主体应竭力消除的理解的障碍,而且是理解不可缺少的前提:我们的过去不仅使我们有了体验的可能性,同时也是我们理解的基础,“理解本身不是被视为主体性的一种行为,而是进入传播之中,过去和现在在此不断地调和”。23 经过这样的“视域融合”,解释学避免了纯粹主观和客观的解释,并且在不断的“理解的循环”中,“存在”得以被理解而“此在”之偏见也不断得到重估与修正,由此文本的意义和理解者在不断的交互影响的过程中意识到自己的历史性和有限性,并不断地向着未来筹划。24 从伽氏的解释学理论我们发现,伽达默尔解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