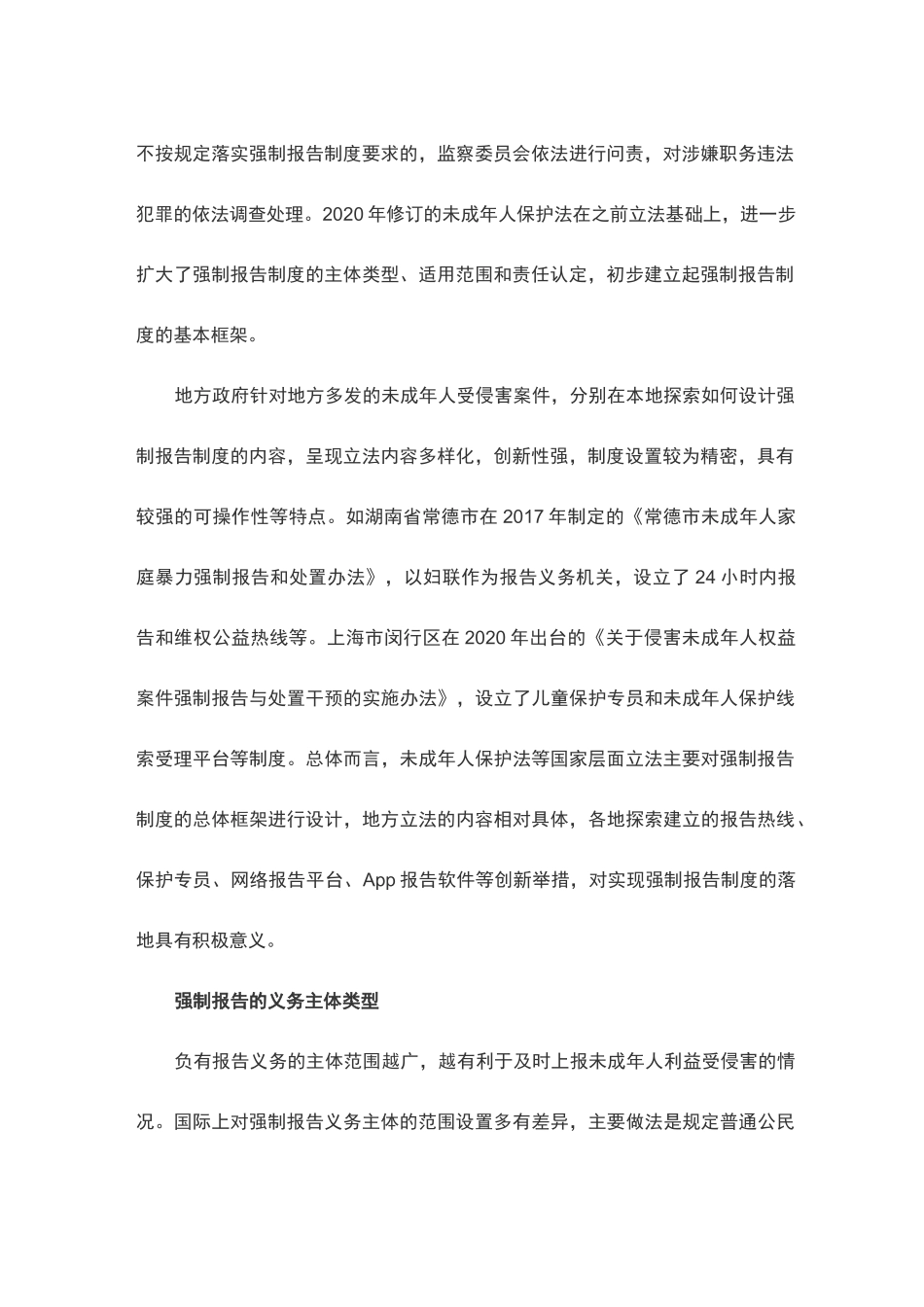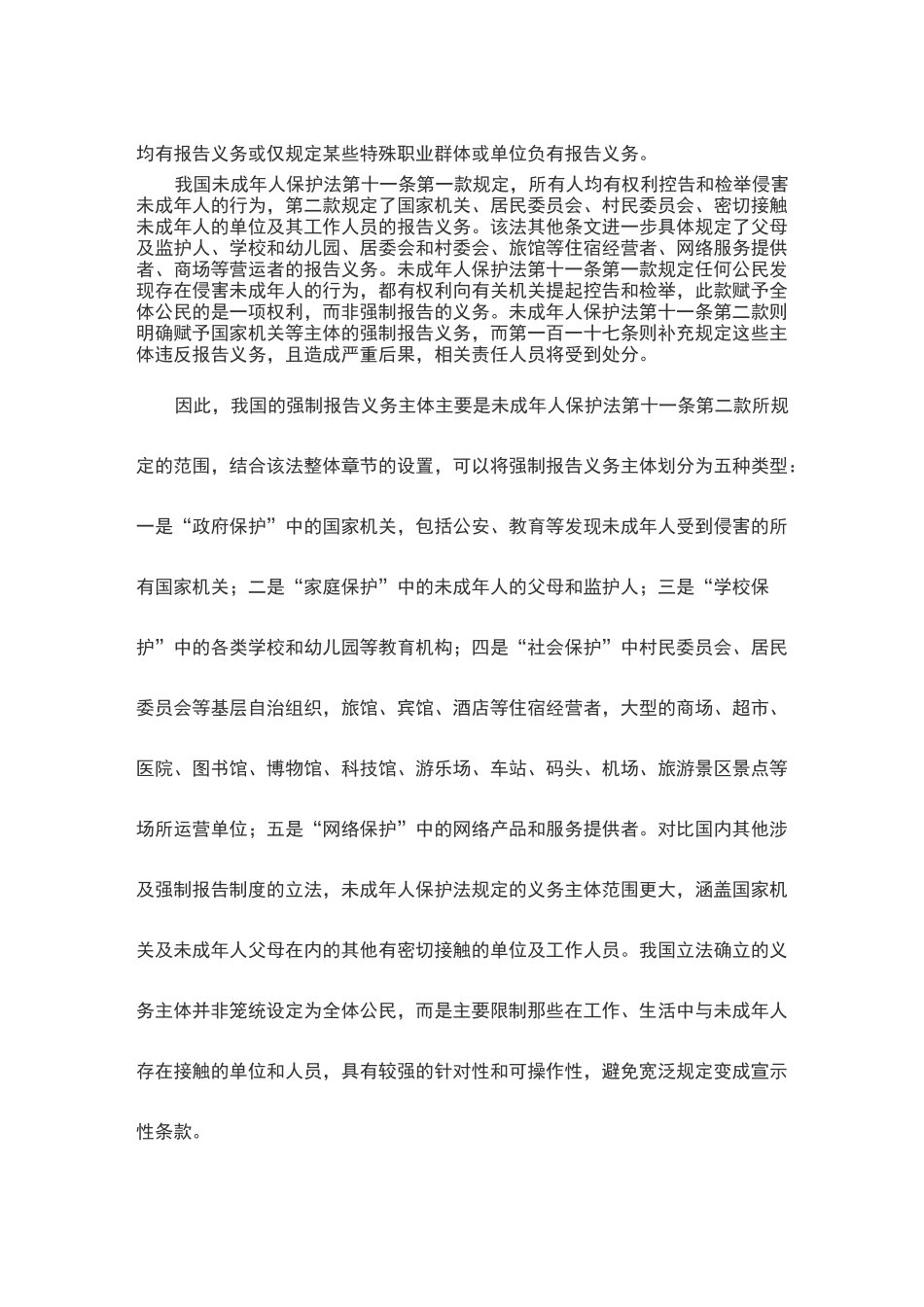未成年强制报告制度简报强制报告制度的立法模式选择国内对强制报告制度主要采取国家和地方分别立法模式,国家层面的立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部分立法条文中开始出现强制报告制度的雏形,到专门性的强制报告制度立法,再到强制报告制度的框架内容逐步健全,前后历经了 20余年的探索。早在 1991 年未成年人保护法颁布之际,其就原则性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向有关部门报告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行为。2013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明确,对未成年人负有特殊义务的单位及个人有义务向公检法报告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2014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印发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要求学校、医院、基层自治组织和社会服务机构等有义务向公安机关报告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行为,类似规定还出现在后续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等立法之中。2020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监察委员会、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明确,检察机关对强制报告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法律监督,发现相关单位执行、监管不力的,可通过发出检察建议书等方式进行监督纠正。对公职人员长期不重视,不按规定落实强制报告制度要求的,监察委员会依法进行问责,对涉嫌职务违法犯罪的依法调查处理。2020 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在之前立法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强制报告制度的主体类型、适用范围和责任认定,初步建立起强制报告制度的基本框架。地方政府针对地方多发的未成年人受侵害案件,分别在本地探索如何设计强制报告制度的内容,呈现立法内容多样化,创新性强,制度设置较为精密,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等特点。如湖南省常德市在 2017 年制定的《常德市未成年人家庭暴力强制报告和处置办法》,以妇联作为报告义务机关,设立了 24 小时内报告和维权公益热线等。上海市闵行区在 2020 年出台的《关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强制报告与处置干预的实施办法》,设立了儿童保护专员和未成年人保护线索受理平台等制度。总体而言,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国家层面立法主要对强制报告制度的总体框架进行设计,地方立法的内容相对具体,各地探索建立的报告热线、保护专员、网络报告平台、App 报告软件等创新举措,对实现强制报告制度的落地具有积极意义。强制报告的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