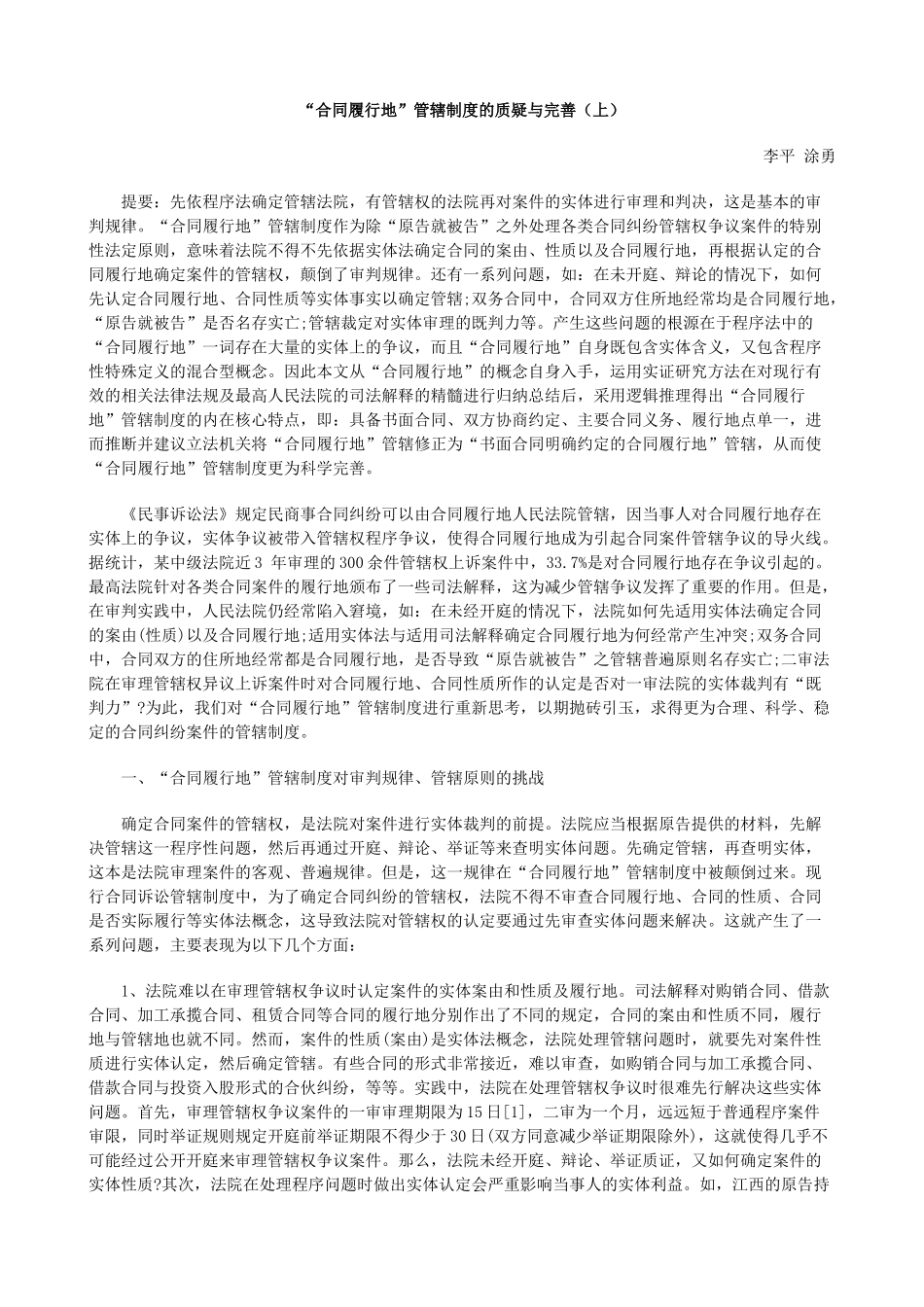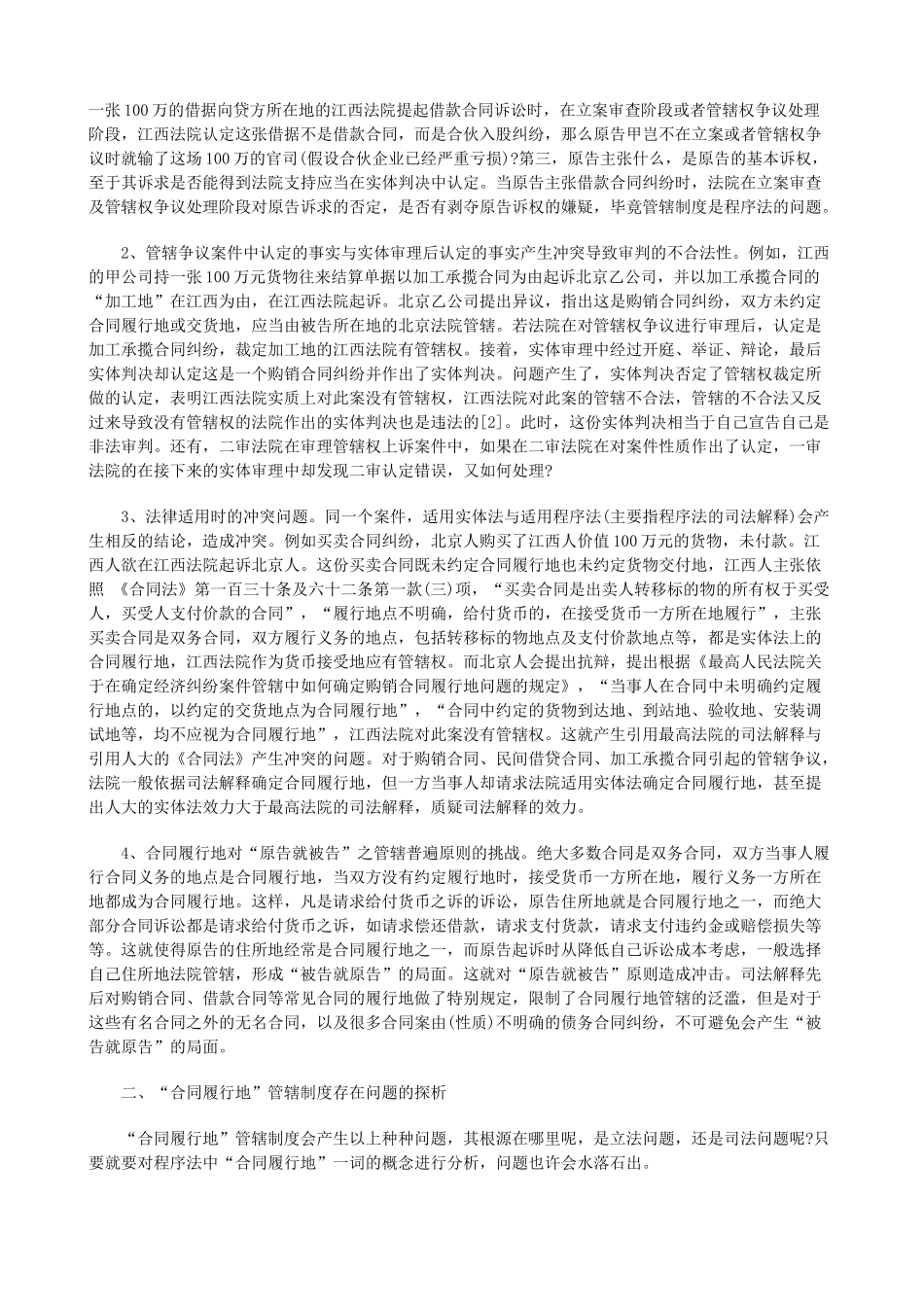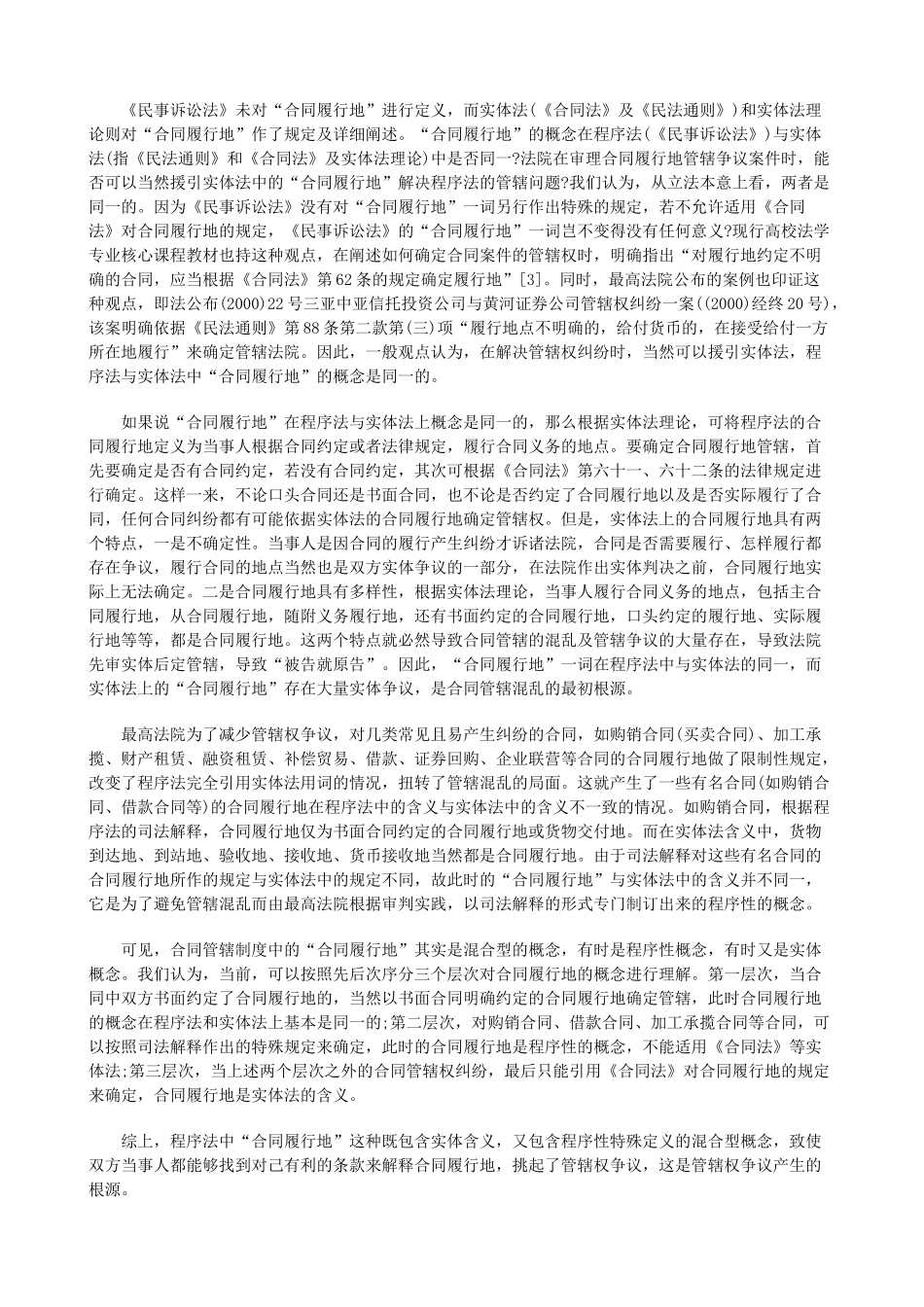“合同履行地”管辖制度的质疑与完善(上) 李平 涂勇 提要:先依程序法确定管辖法院,有管辖权的法院再对案件的实体进行审理和判决,这是基本的审判规律。“合同履行地”管辖制度作为除“原告就被告”之外处理各类合同纠纷管辖权争议案件的特别性法定原则,意味着法院不得不先依据实体法确定合同的案由、性质以及合同履行地,再根据认定的合同履行地确定案件的管辖权,颠倒了审判规律。还有一系列问题,如:在未开庭、辩论的情况下,如何先认定合同履行地、合同性质等实体事实以确定管辖;双务合同中,合同双方住所地经常均是合同履行地,“原告就被告”是否名存实亡;管辖裁定对实体审理的既判力等。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程序法中的“合同履行地”一词存在大量的实体上的争议,而且“合同履行地”自身既包含实体含义,又包含程序性特殊定义的混合型概念。因此本文从“合同履行地”的概念自身入手,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在对现行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的精髓进行归纳总结后,采用逻辑推理得出“合同履行地”管辖制度的内在核心特点,即:具备书面合同、双方协商约定、主要合同义务、履行地点单一,进而推断并建议立法机关将“合同履行地”管辖修正为“书面合同明确约定的合同履行地”管辖,从而使“合同履行地”管辖制度更为科学完善。 《民事诉讼法》规定民商事合同纠纷可以由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因当事人对合同履行地存在实体上的争议,实体争议被带入管辖权程序争议,使得合同履行地成为引起合同案件管辖争议的导火线。据统计,某中级法院近 3 年审理的 300 余件管辖权上诉案件中,33.7%是对合同履行地存在争议引起的。最高法院针对各类合同案件的履行地颁布了一些司法解释,这为减少管辖争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仍经常陷入窘境,如:在未经开庭的情况下,法院如何先适用实体法确定合同的案由(性质)以及合同履行地;适用实体法与适用司法解释确定合同履行地为何经常产生冲突;双务合同中,合同双方的住所地经常都是合同履行地,是否导致“原告就被告”之管辖普遍原则名存实亡;二审法院在审理管辖权异议上诉案件时对合同履行地、合同性质所作的认定是否对一审法院的实体裁判有“既判力”?为此,我们对“合同履行地”管辖制度进行重新思考,以期抛砖引玉,求得更为合理、科学、稳定的合同纠纷案件的管辖制度。 一、“合同履行地”管辖制度对审判规律、管辖原则的挑战 确定合同案件的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