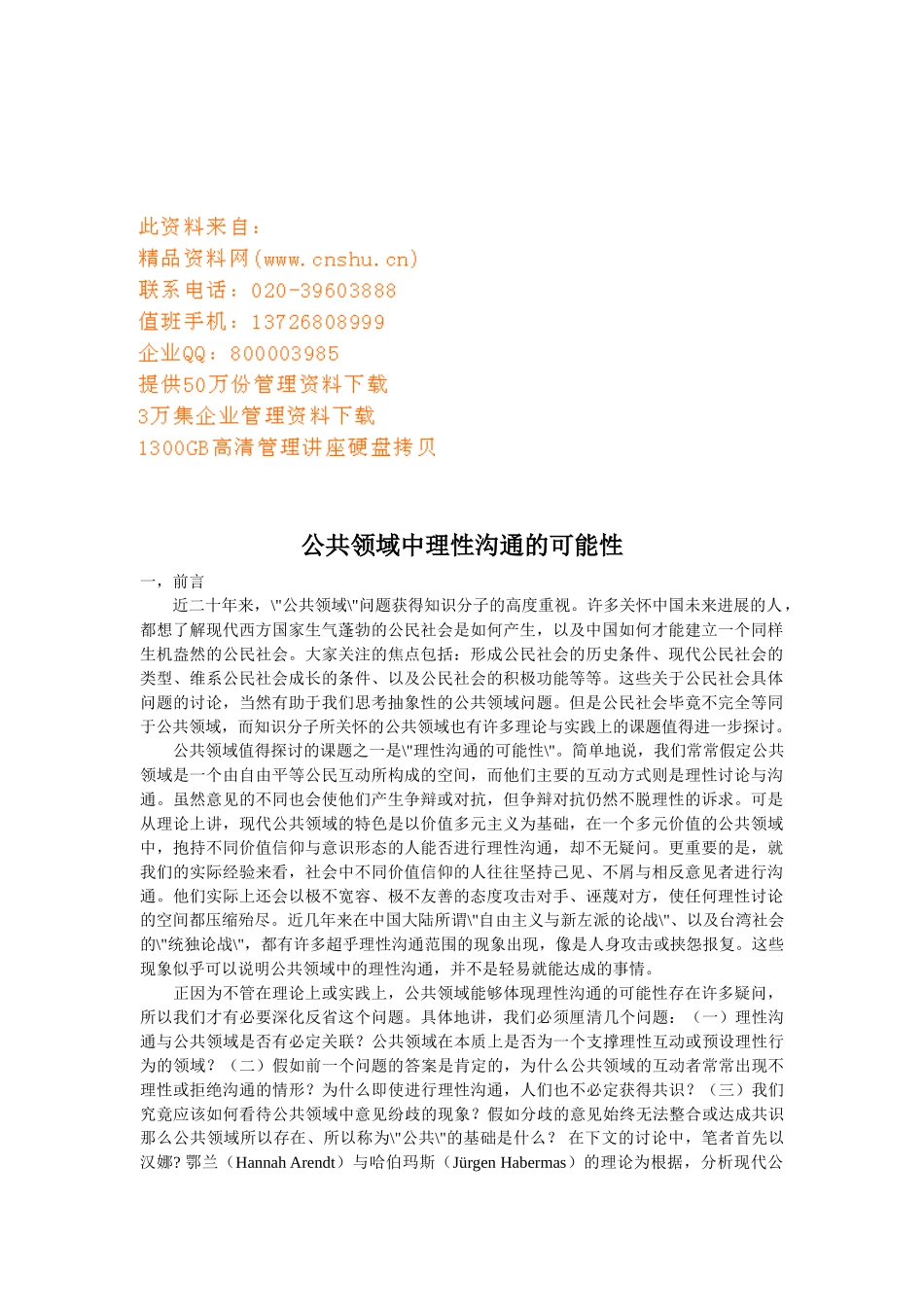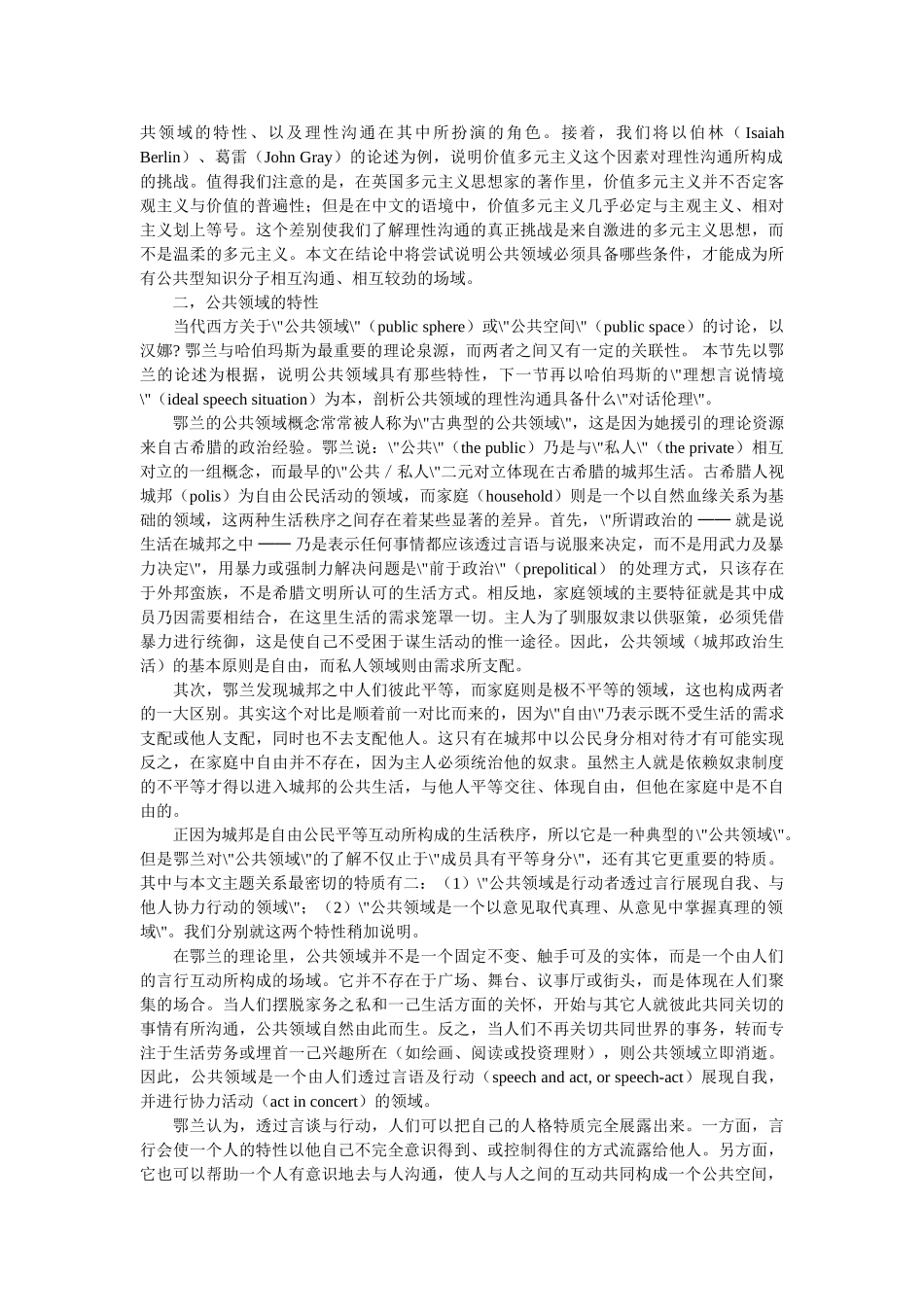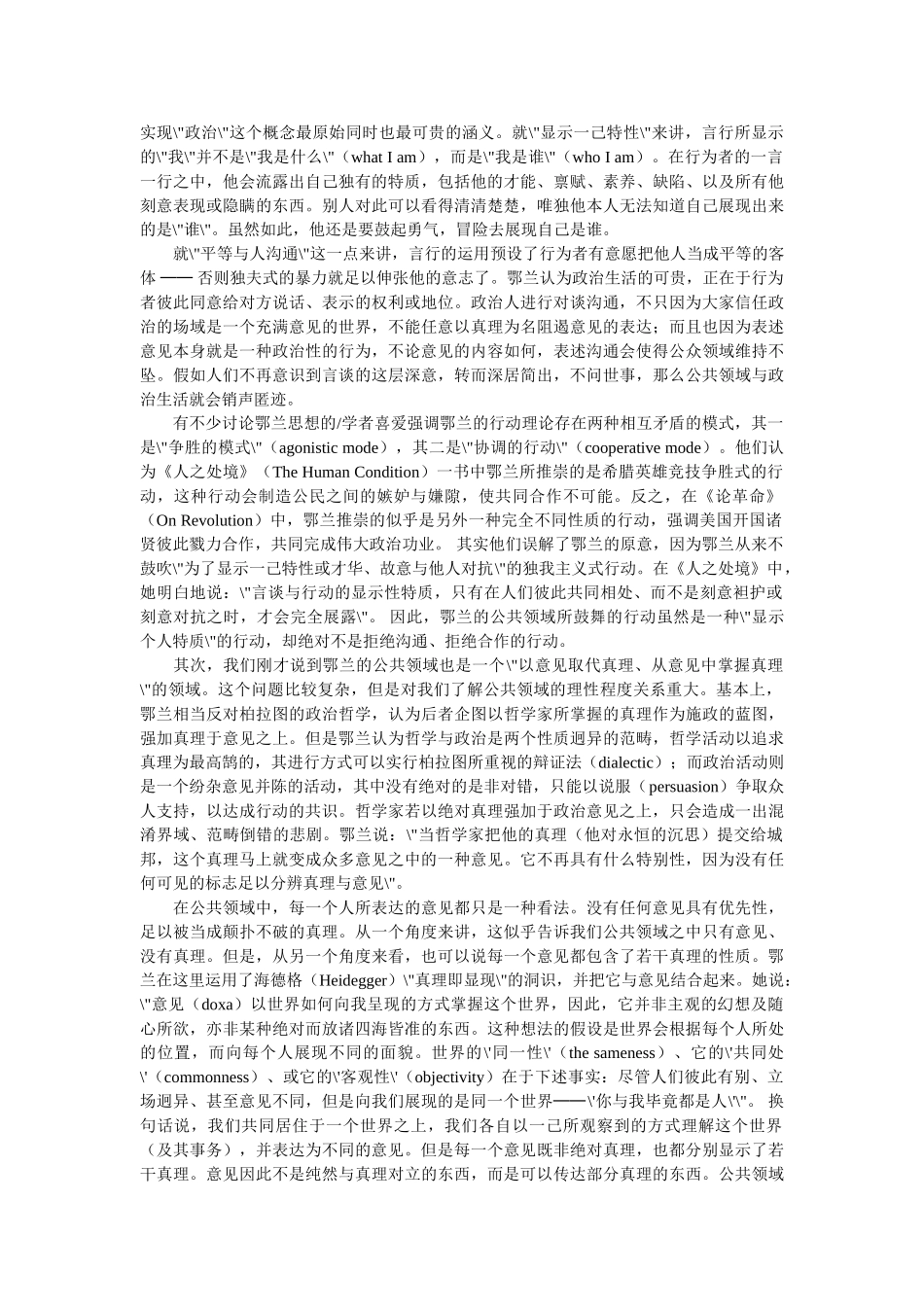公共领域中理性沟通的可能性一,前言 近二十年来,\"公共领域\"问题获得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许多关怀中国未来进展的人,都想了解现代西方国家生气蓬勃的公民社会是如何产生,以及中国如何才能建立一个同样生机盎然的公民社会。大家关注的焦点包括:形成公民社会的历史条件、现代公民社会的类型、维系公民社会成长的条件、以及公民社会的积极功能等等。这些关于公民社会具体问题的讨论,当然有助于我们思考抽象性的公共领域问题。但是公民社会毕竟不完全等同于公共领域,而知识分子所关怀的公共领域也有许多理论与实践上的课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公共领域值得探讨的课题之一是\"理性沟通的可能性\"。简单地说,我们常常假定公共领域是一个由自由平等公民互动所构成的空间,而他们主要的互动方式则是理性讨论与沟通。虽然意见的不同也会使他们产生争辩或对抗,但争辩对抗仍然不脱理性的诉求。可是从理论上讲,现代公共领域的特色是以价值多元主义为基础,在一个多元价值的公共领域中,抱持不同价值信仰与意识形态的人能否进行理性沟通,却不无疑问。更重要的是,就我们的实际经验来看,社会中不同价值信仰的人往往坚持己见、不屑与相反意见者进行沟通。他们实际上还会以极不宽容、极不友善的态度攻击对手、诬蔑对方,使任何理性讨论的空间都压缩殆尽。近几年来在中国大陆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以及台湾社会的\"统独论战\",都有许多超乎理性沟通范围的现象出现,像是人身攻击或挟怨报复。这些现象似乎可以说明公共领域中的理性沟通,并不是轻易就能达成的事情。 正因为不管在理论上或实践上,公共领域能够体现理性沟通的可能性存在许多疑问,所以我们才有必要深化反省这个问题。具体地讲,我们必须厘清几个问题:(一)理性沟通与公共领域是否有必定关联?公共领域在本质上是否为一个支撑理性互动或预设理性行为的领域?(二)假如前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公共领域的互动者常常出现不理性或拒绝沟通的情形?为什么即使进行理性沟通,人们也不必定获得共识?(三)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公共领域中意见纷歧的现象?假如分歧的意见始终无法整合或达成共识那么公共领域所以存在、所以称为\"公共\"的基础是什么? 在下文的讨论中,笔者首先以汉娜? 鄂兰(Hannah Arendt)与哈伯玛斯(Jürgen Habermas)的理论为根据,分析现代公共领域的特性、以及理性沟通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接着,我们将以伯林( Isaiah Berlin)、葛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