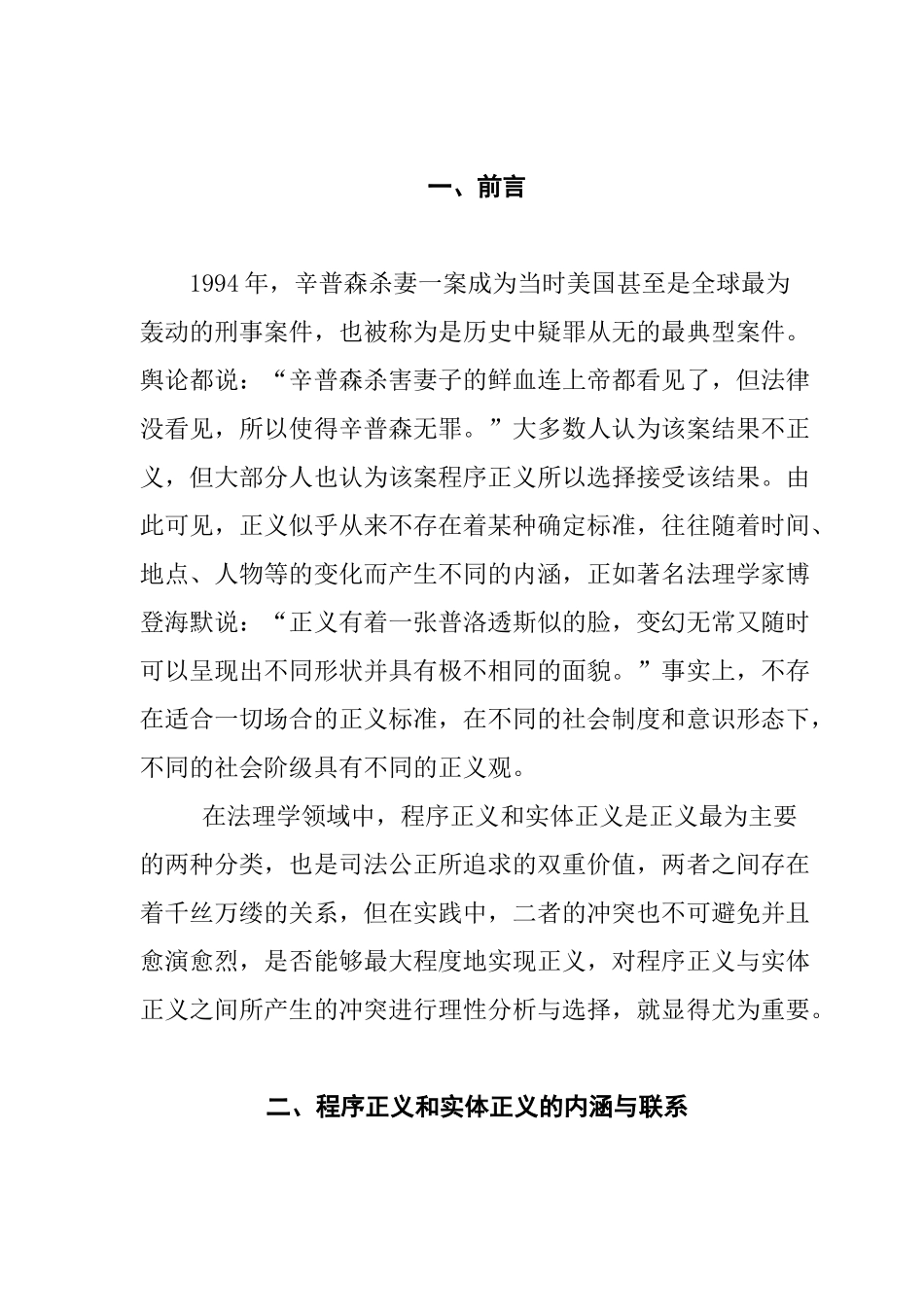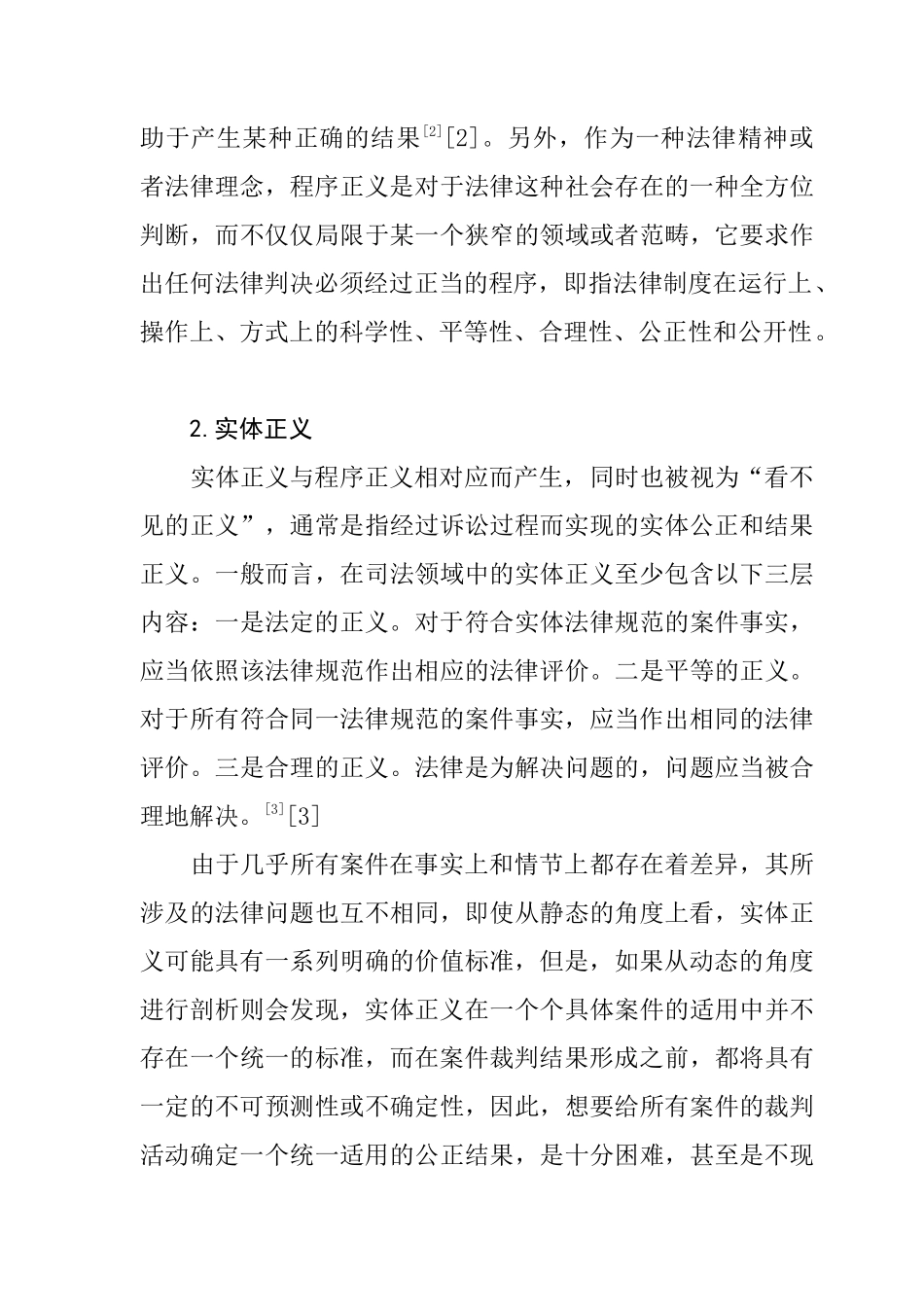一、前言 1994 年,辛普森杀妻一案成为当时美国甚至是全球最为轰动的刑事案件,也被称为是历史中疑罪从无的最典型案件。舆论都说:“辛普森杀害妻子的鲜血连上帝都看见了,但法律没看见,所以使得辛普森无罪。”大多数人认为该案结果不正义,但大部分人也认为该案程序正义所以选择接受该结果。由此可见,正义似乎从来不存在着某种确定标准,往往随着时间、地点、人物等的变化而产生不同的内涵,正如著名法理学家博登海默说:“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又随时可以呈现出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事实上,不存在适合一切场合的正义标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下,不同的社会阶级具有不同的正义观。 在法理学领域中,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是正义最为主要的两种分类,也是司法公正所追求的双重价值,两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在实践中,二者的冲突也不可避免并且愈演愈烈,是否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正义,对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之间所产生的冲突进行理性分析与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二、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内涵与联系(一)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内涵1.程序正义 英国的自然正义和美国的正当程序是程序正义的两大基本渊源,自然正义即不作自己的法官和听取当事人的陈述,主要可以体现在对裁判过程的约束;正当程序即实体性的正当法律程序和程序性的正当法律程序,其适用则扩充到了立法领域,相对于自然正义而言较为广泛。在英美法系的法律文化传统和观念中,程序正义被人们视为“看得见的正义”,正如法律谚语所说:“正义不仅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实质上就是指法律程序的正义与裁判过程的公平。 美国著名学者罗尔斯在其所著的《正义论》中提出并分析了程序正义的三种分类:纯粹的程序正义、完善的程序正义以及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在该文献中,其主要论述了纯粹的程序正义,这一观点认为:“程序正义之外没有独立的判断实体是否正义的标准,只要程序是公正的,就认为其结果肯定是公正的,也是可以接受的,程序正义可以决定实体正义,具有其独立的价值”[1][1]。虽然这种说法过于绝对,但却创造性的提出了程序独立价值观点,给予了程序正义的内涵一种崭新启示:一项法律程序或者法律实施过程是否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应当看它能否保护一些独立的内在价值,而不是仅仅看它能否有助于产生某种正确的结果[2][2]。另外,作为一种法律精神或者法律理念,程序正义是对于法律这种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