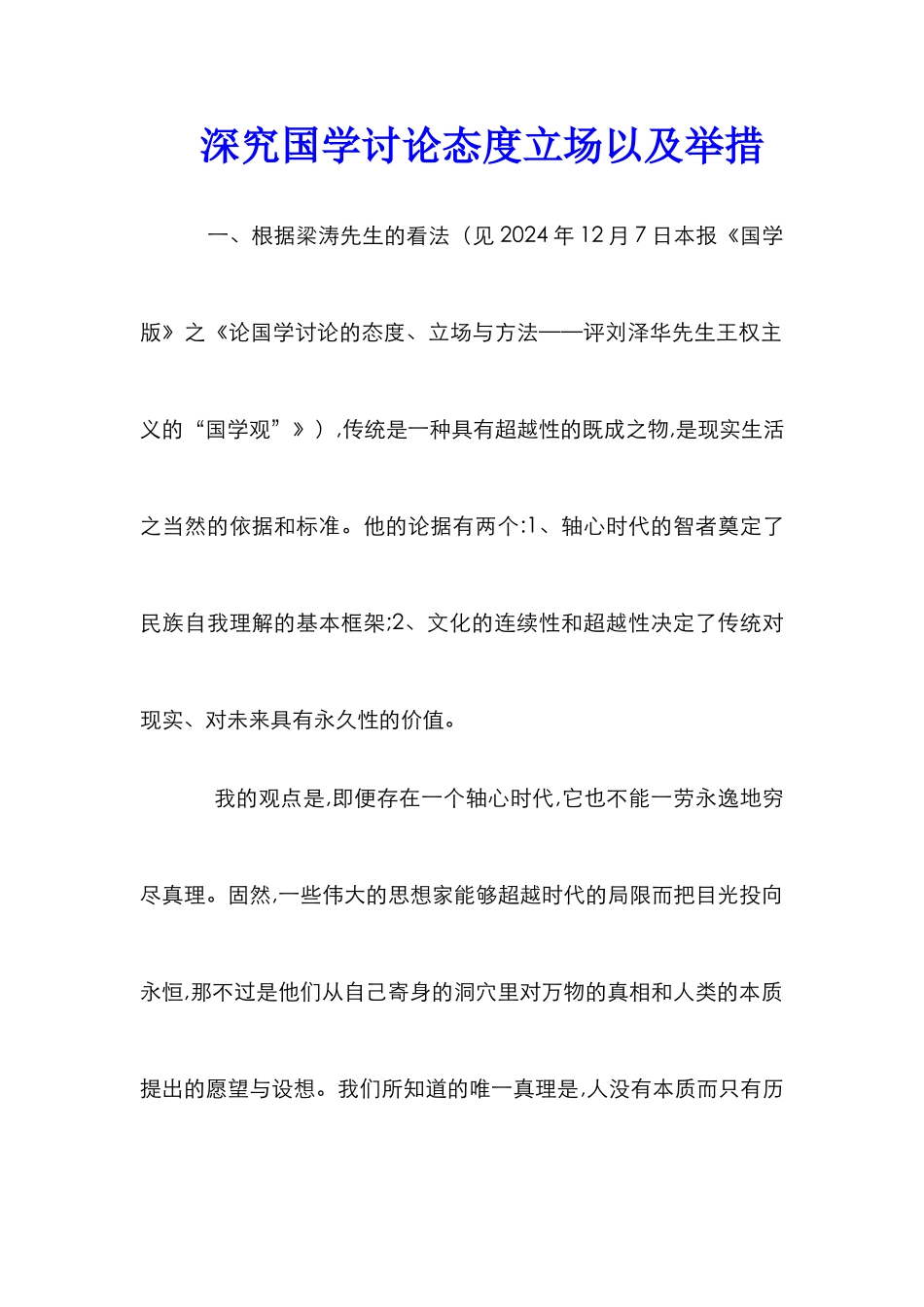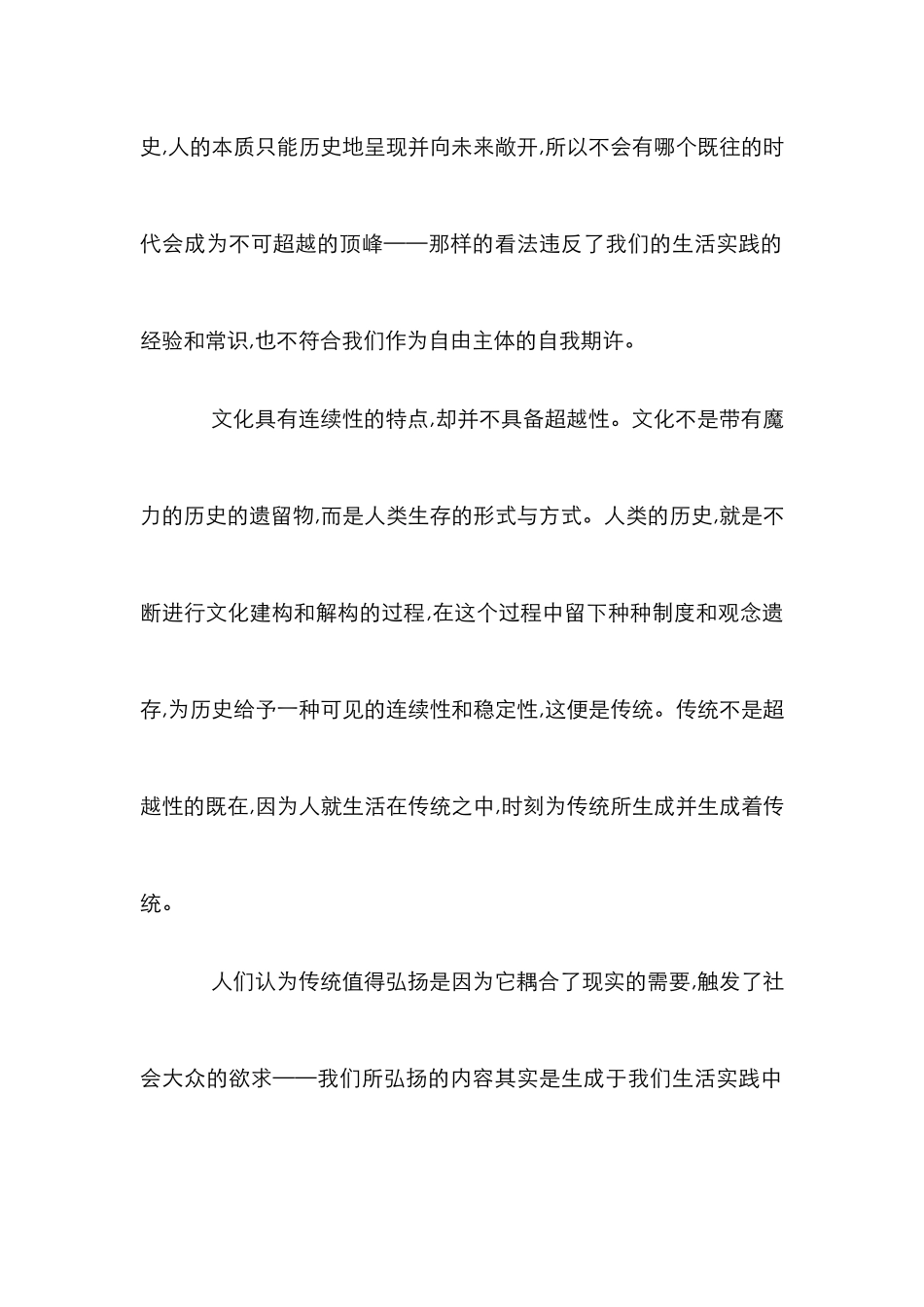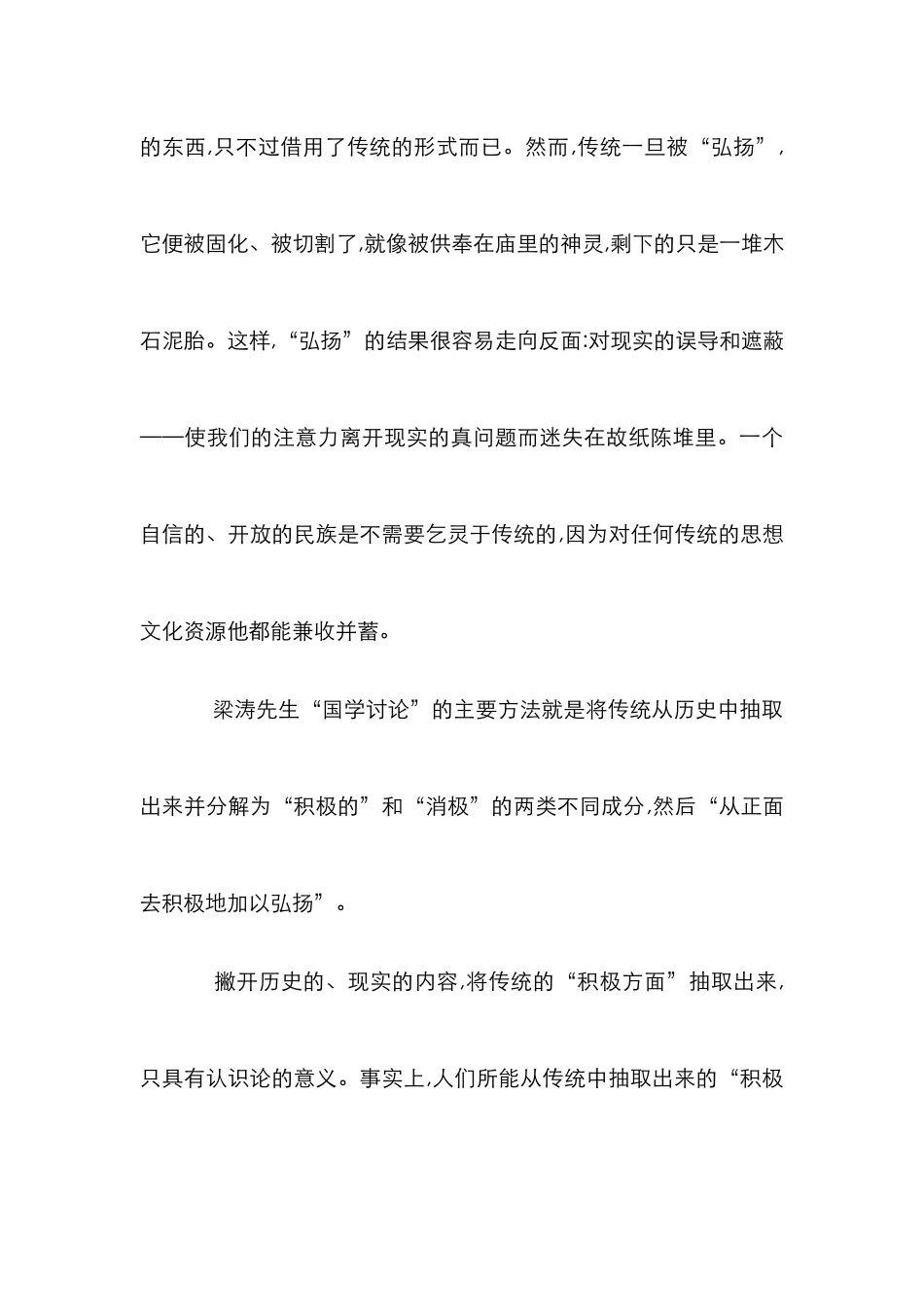深究国学讨论态度立场以及举措 一、根据梁涛先生的看法(见 2024 年 12 月 7 日本报《国学版》之《论国学讨论的态度、立场与方法——评刘泽华先生王权主义的“国学观”》),传统是一种具有超越性的既成之物,是现实生活之当然的依据和标准。他的论据有两个:1、轴心时代的智者奠定了民族自我理解的基本框架;2、文化的连续性和超越性决定了传统对现实、对未来具有永久性的价值。 我的观点是,即便存在一个轴心时代,它也不能一劳永逸地穷尽真理。固然,一些伟大的思想家能够超越时代的局限而把目光投向永恒,那不过是他们从自己寄身的洞穴里对万物的真相和人类的本质提出的愿望与设想。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真理是,人没有本质而只有历史,人的本质只能历史地呈现并向未来敞开,所以不会有哪个既往的时代会成为不可超越的顶峰——那样的看法违反了我们的生活实践的经验和常识,也不符合我们作为自由主体的自我期许。 文化具有连续性的特点,却并不具备超越性。文化不是带有魔力的历史的遗留物,而是人类生存的形式与方式。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进行文化建构和解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留下种种制度和观念遗存,为历史给予一种可见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便是传统。传统不是超越性的既在,因为人就生活在传统之中,时刻为传统所生成并生成着传统。 人们认为传统值得弘扬是因为它耦合了现实的需要,触发了社会大众的欲求——我们所弘扬的内容其实是生成于我们生活实践中的东西,只不过借用了传统的形式而已。然而,传统一旦被“弘扬”,它便被固化、被切割了,就像被供奉在庙里的神灵,剩下的只是一堆木石泥胎。这样,“弘扬”的结果很容易走向反面:对现实的误导和遮蔽——使我们的注意力离开现实的真问题而迷失在故纸陈堆里。一个自信的、开放的民族是不需要乞灵于传统的,因为对任何传统的思想文化资源他都能兼收并蓄。 梁涛先生“国学讨论”的主要方法就是将传统从历史中抽取出来并分解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类不同成分,然后“从正面去积极地加以弘扬”。 撇开历史的、现实的内容,将传统的“积极方面”抽取出来,只具有认识论的意义。事实上,人们所能从传统中抽取出来的“积极的”东西,只是一些有待发挥的价值信条和有待填充的概念形式而已。固然,它们曾经内涵着鲜活的现实内容,但这些“精华”的文化种子只有扎根于人们生产和生存斗争的社会实践并接受了现代价值的灌注,才会重新获得生机。人们可以拿这些传统的东西去“转化”,去“返本开新”,只是不要忘了那是“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