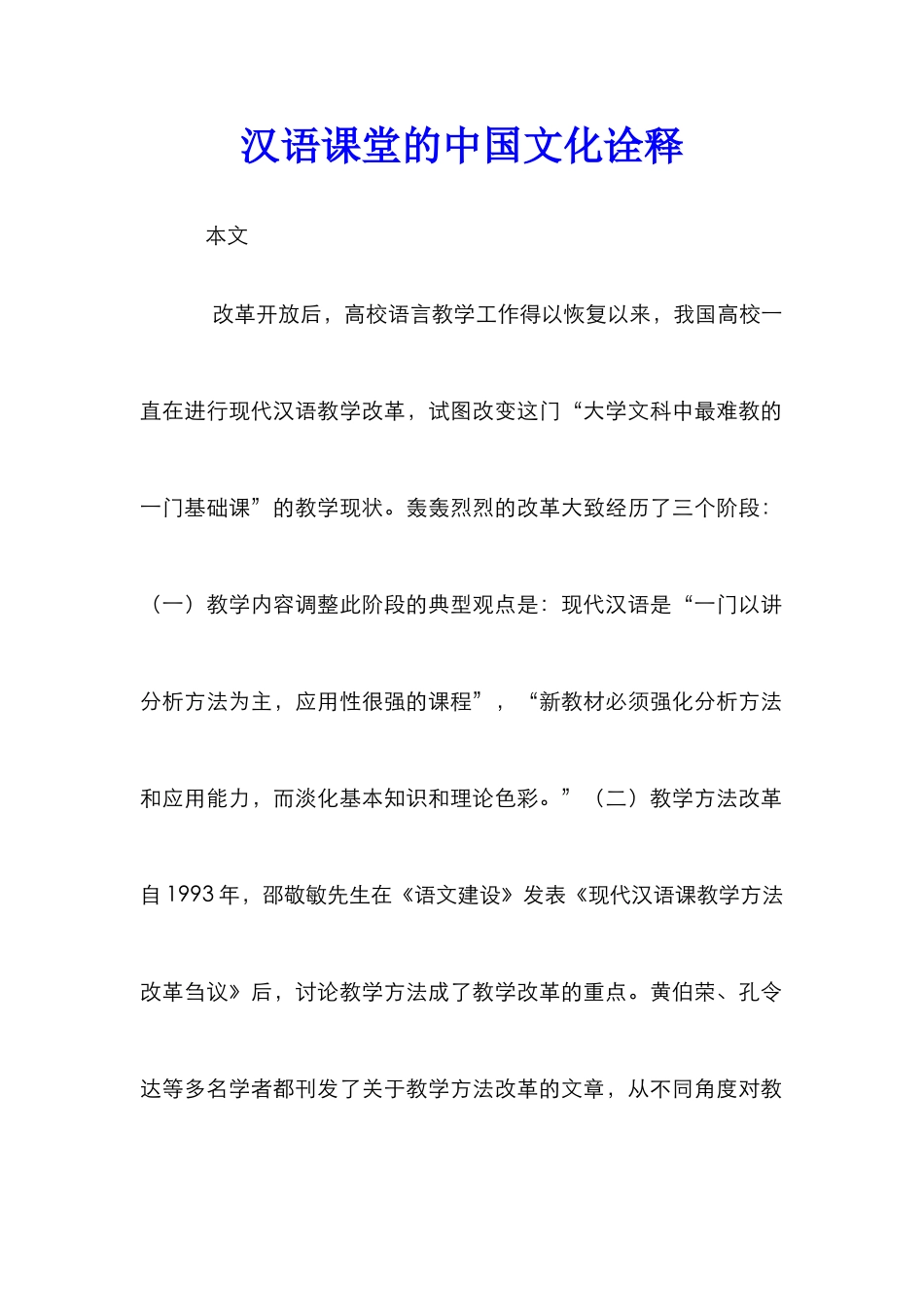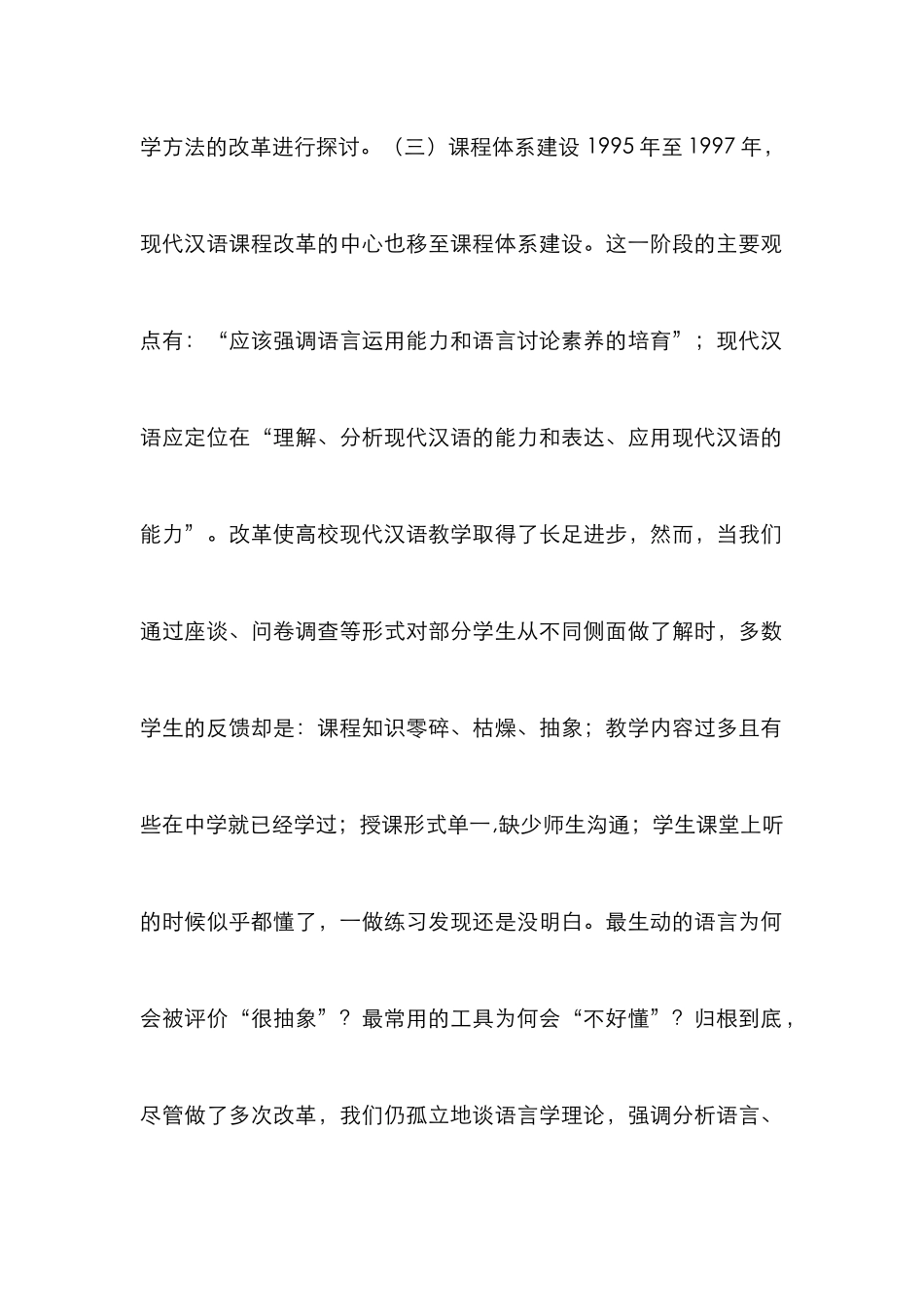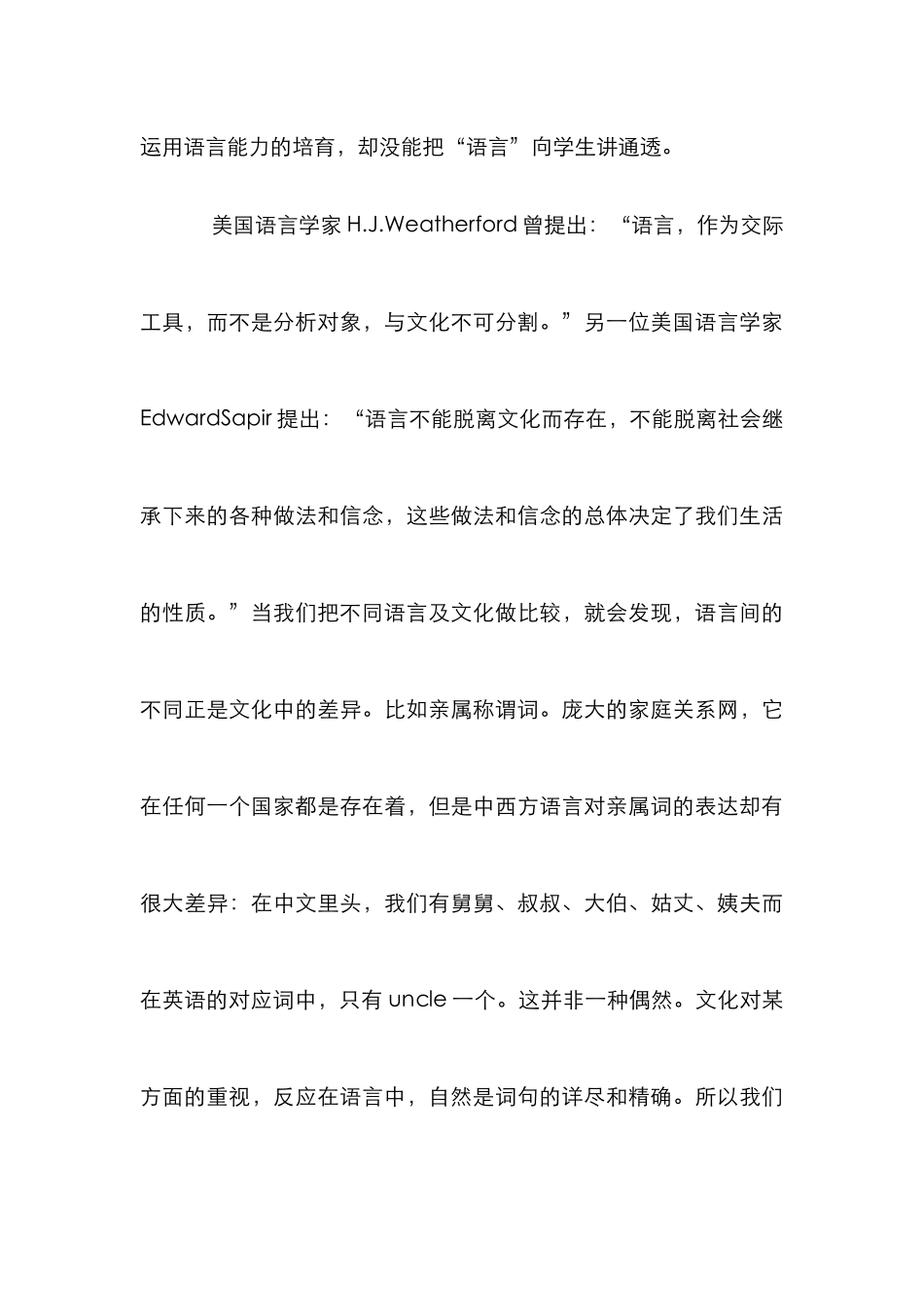汉语课堂的中国文化诠释 本文 改革开放后,高校语言教学工作得以恢复以来,我国高校一直在进行现代汉语教学改革,试图改变这门“大学文科中最难教的一门基础课”的教学现状。轰轰烈烈的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教学内容调整此阶段的典型观点是:现代汉语是“一门以讲分析方法为主,应用性很强的课程”,“新教材必须强化分析方法和应用能力,而淡化基本知识和理论色彩。”(二)教学方法改革自 1993 年,邵敬敏先生在《语文建设》发表《现代汉语课教学方法改革刍议》后,讨论教学方法成了教学改革的重点。黄伯荣、孔令达等多名学者都刊发了关于教学方法改革的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教学方法的改革进行探讨。(三)课程体系建设 1995 年至 1997 年,现代汉语课程改革的中心也移至课程体系建设。这一阶段的主要观点有:“应该强调语言运用能力和语言讨论素养的培育”;现代汉语应定位在“理解、分析现代汉语的能力和表达、应用现代汉语的能力”。改革使高校现代汉语教学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当我们通过座谈、问卷调查等形式对部分学生从不同侧面做了解时,多数学生的反馈却是:课程知识零碎、枯燥、抽象;教学内容过多且有些在中学就已经学过;授课形式单一,缺少师生沟通;学生课堂上听的时候似乎都懂了,一做练习发现还是没明白。最生动的语言为何会被评价“很抽象”?最常用的工具为何会“不好懂”?归根到底,尽管做了多次改革,我们仍孤立地谈语言学理论,强调分析语言、运用语言能力的培育,却没能把“语言”向学生讲通透。 美国语言学家 H.J.Weatherford 曾提出:“语言,作为交际工具,而不是分析对象,与文化不可分割。”另一位美国语言学家EdwardSapir 提出:“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继承下来的各种做法和信念,这些做法和信念的总体决定了我们生活的性质。”当我们把不同语言及文化做比较,就会发现,语言间的不同正是文化中的差异。比如亲属称谓词。庞大的家庭关系网,它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存在着,但是中西方语言对亲属词的表达却有很大差异:在中文里头,我们有舅舅、叔叔、大伯、姑丈、姨夫而在英语的对应词中,只有 uncle 一个。这并非一种偶然。文化对某方面的重视,反应在语言中,自然是词句的详尽和精确。所以我们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甚至,“语言是文化的凝聚体”。 正是因为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如此紧密,语言的学习,无法脱离文化教授独立存在。事实上,我们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摆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