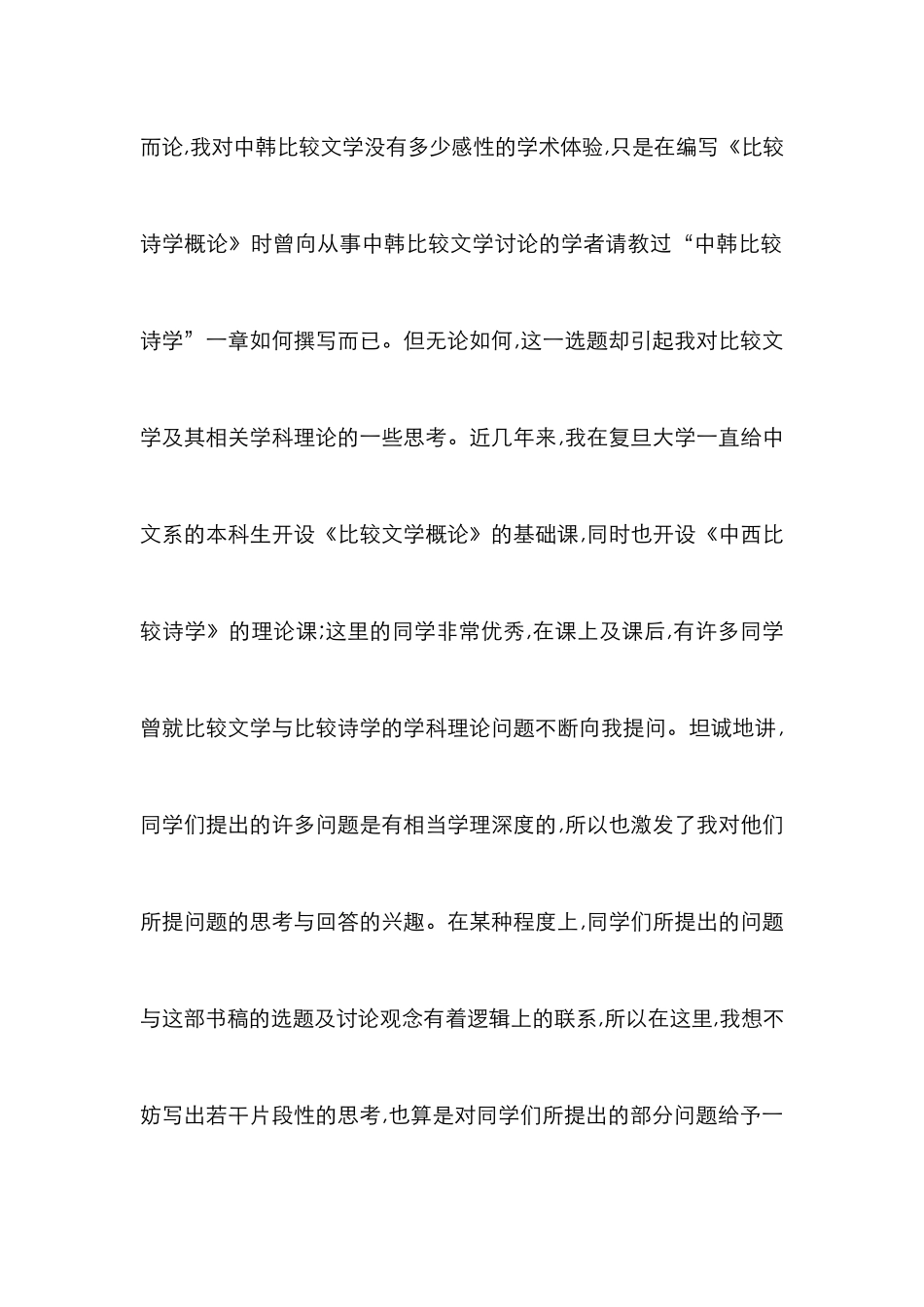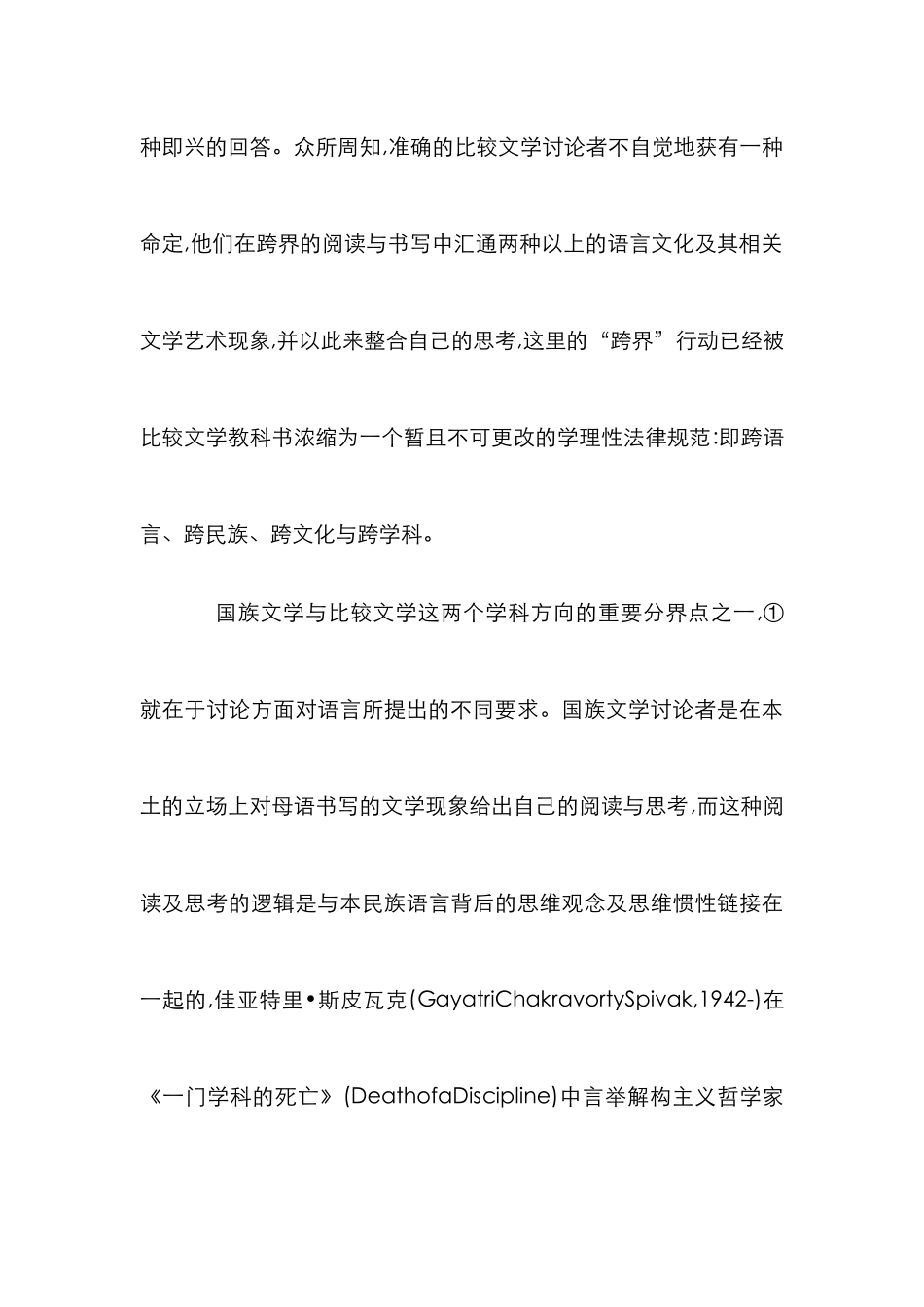比较文学与第三种文学批判思索 不同于国族文学的是,比较文学的确需要明晰、准确且自洽的学科理论意识。对于一位从事比较文学教学与讨论的学者来说,你可以在现有比较文学的多种学科理论体系中择取自己的立场,可以不同意别人的观点,然而,你必定曾经遭遇过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冲突与对话。在这种冲突与对话中思考过与沉淀过,这样才可能获有一种学科的专业意识支撑你的表达与讨论,不至于一开口、一落笔让学界感到你是专业外的学者。 前一段时间,因一次偶然的学术沟通,我翻阅了一部关于中韩比较文学讨论的书稿,① 这部书稿把中国当代作家张承志的《黑骏马》与韩国现代作家金承钰的《雾津纪行》进行了比较讨论。凭心而论,我对中韩比较文学没有多少感性的学术体验,只是在编写《比较诗学概论》时曾向从事中韩比较文学讨论的学者请教过“中韩比较诗学”一章如何撰写而已。但无论如何,这一选题却引起我对比较文学及其相关学科理论的一些思考。近几年来,我在复旦大学一直给中文系的本科生开设《比较文学概论》的基础课,同时也开设《中西比较诗学》的理论课;这里的同学非常优秀,在课上及课后,有许多同学曾就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的学科理论问题不断向我提问。坦诚地讲,同学们提出的许多问题是有相当学理深度的,所以也激发了我对他们所提问题的思考与回答的兴趣。在某种程度上,同学们所提出的问题与这部书稿的选题及讨论观念有着逻辑上的联系,所以在这里,我想不妨写出若干片段性的思考,也算是对同学们所提出的部分问题给予一种即兴的回答。众所周知,准确的比较文学讨论者不自觉地获有一种命定,他们在跨界的阅读与书写中汇通两种以上的语言文化及其相关文学艺术现象,并以此来整合自己的思考,这里的“跨界”行动已经被比较文学教科书浓缩为一个暂且不可更改的学理性法律规范:即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与跨学科。 国族文学与比较文学这两个学科方向的重要分界点之一,①就在于讨论方面对语言所提出的不同要求。国族文学讨论者是在本土的立场上对母语书写的文学现象给出自己的阅读与思考,而这种阅读及思考的逻辑是与本民族语言背后的思维观念及思维惯性链接在一起的,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ChakravortySpivak,1942-)在《一门学科的死亡》(DeathofaDiscipline)中言举解构主义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Derrida,1930-2024)时说明了这一点:“雅克•德里达是哲学家中的天才,他认为,‘哲学观念不可能超越习惯的差异。’这种领悟力不仅仅适用于法语、德语,或者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