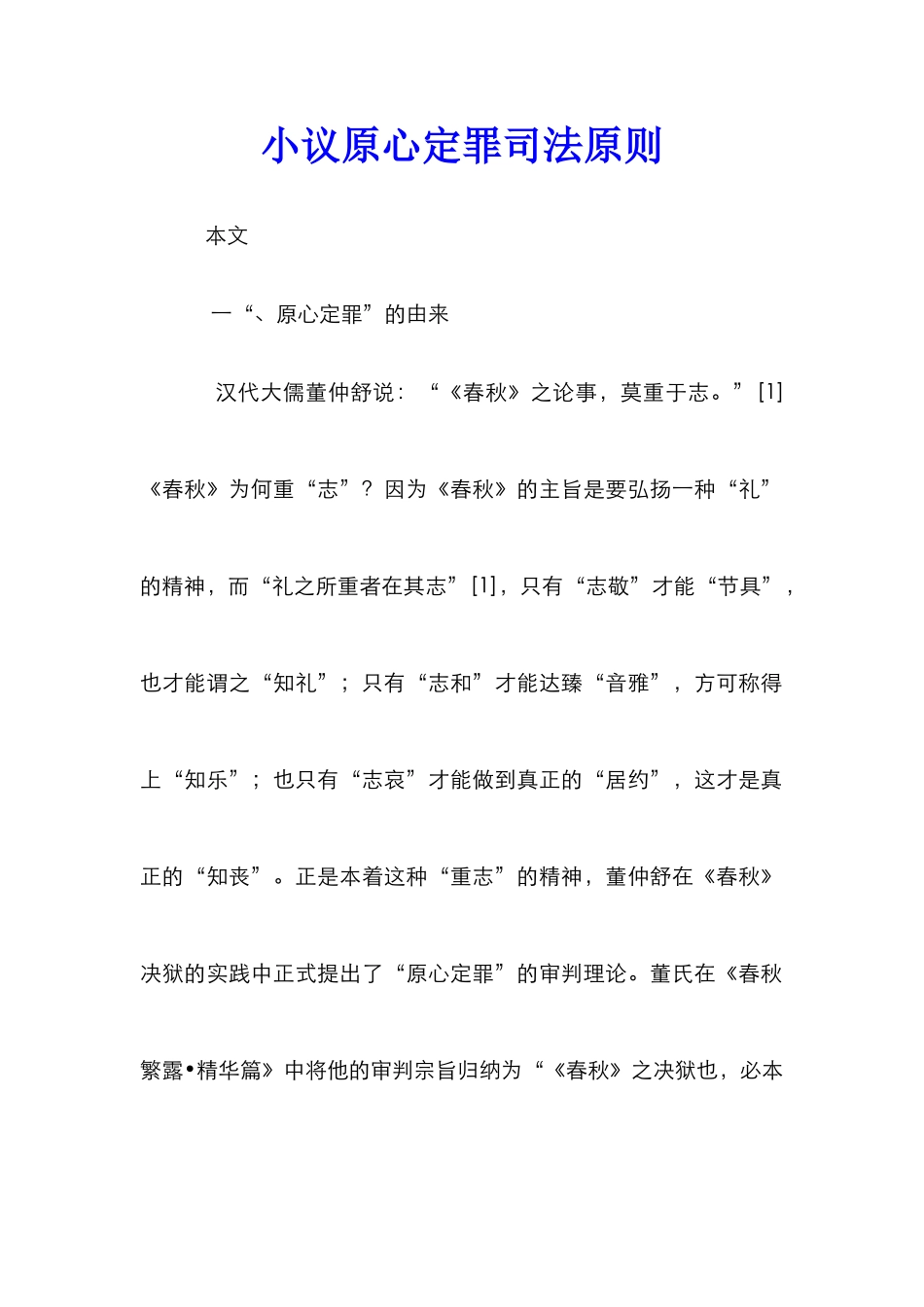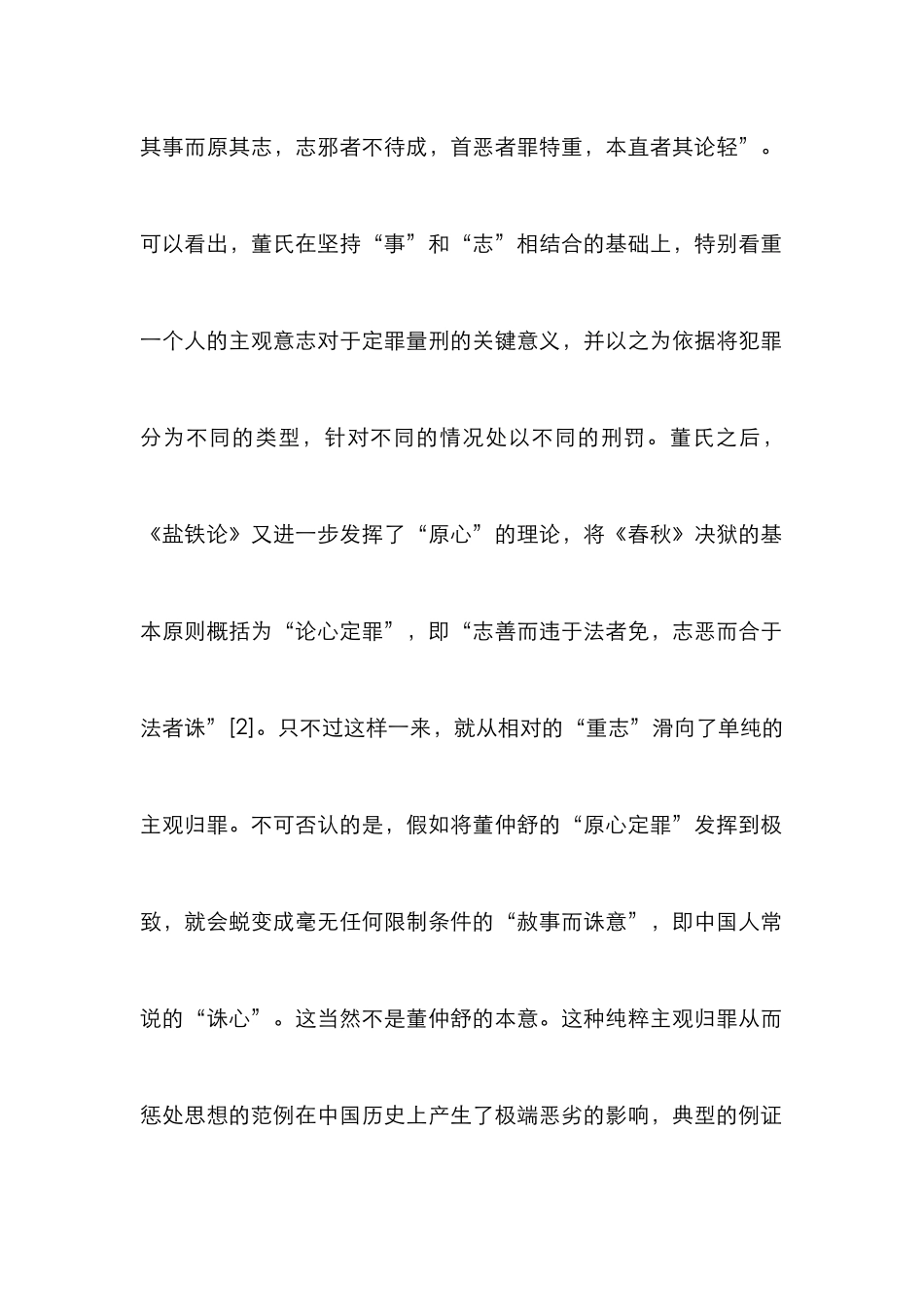小议原心定罪司法原则 本文 一“、原心定罪”的由来 汉代大儒董仲舒说:“《春秋》之论事,莫重于志。”[1]《春秋》为何重“志”?因为《春秋》的主旨是要弘扬一种“礼”的精神,而“礼之所重者在其志”[1],只有“志敬”才能“节具”,也才能谓之“知礼”;只有“志和”才能达臻“音雅”,方可称得上“知乐”;也只有“志哀”才能做到真正的“居约”,这才是真正的“知丧”。正是本着这种“重志”的精神,董仲舒在《春秋》决狱的实践中正式提出了“原心定罪”的审判理论。董氏在《春秋繁露•精华篇》中将他的审判宗旨归纳为“《春秋》之决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可以看出,董氏在坚持“事”和“志”相结合的基础上,特别看重一个人的主观意志对于定罪量刑的关键意义,并以之为依据将犯罪分为不同的类型,针对不同的情况处以不同的刑罚。董氏之后,《盐铁论》又进一步发挥了“原心”的理论,将《春秋》决狱的基本原则概括为“论心定罪”,即“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2]。只不过这样一来,就从相对的“重志”滑向了单纯的主观归罪。不可否认的是,假如将董仲舒的“原心定罪”发挥到极致,就会蜕变成毫无任何限制条件的“赦事而诛意”,即中国人常说的“诛心”。这当然不是董仲舒的本意。这种纯粹主观归罪从而惩处思想的范例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端恶劣的影响,典型的例证就是“腹诽”罪名的问世。同时“,诛心”的观念对于民族性格的塑造和民间心理的形成也影响至深。中国人在评陟人物时总喜爱做“诛心”之论。“诛心”说在当代的新表现,就是动辄对人们的言论文字或行为上纲上线,乱扣大帽子“,文革”中此类事例真是擢发难数。“诛心”的观念的思想根源何在?为何在中国古代能够泛滥成灾?郝铁川认为,儒家的“性善论把人心视为一切美好价值观念的源头,引导人们向内挖掘,使得中国传统的刑法以‘诛心’为目的,即‘论心定罪’”[3]。可是,令笔者疑窦丛生的是,法家虽信奉性恶之说,却同样主张“诛心”,试看韩非子的经典论述“: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又《韩非子•外储说上》云“: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说《春秋》也:善持势者,蚤绝其奸萌。”更证实了儒法两家在钳制思想方面立场的不谋而合。无疑,他们都是主张“绝恶于未萌”[4]的,这也是由他们的学说为专制主义服务的本性决定的。那么,假如说一定要冠以“专制主义的帮凶”的名号的话,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