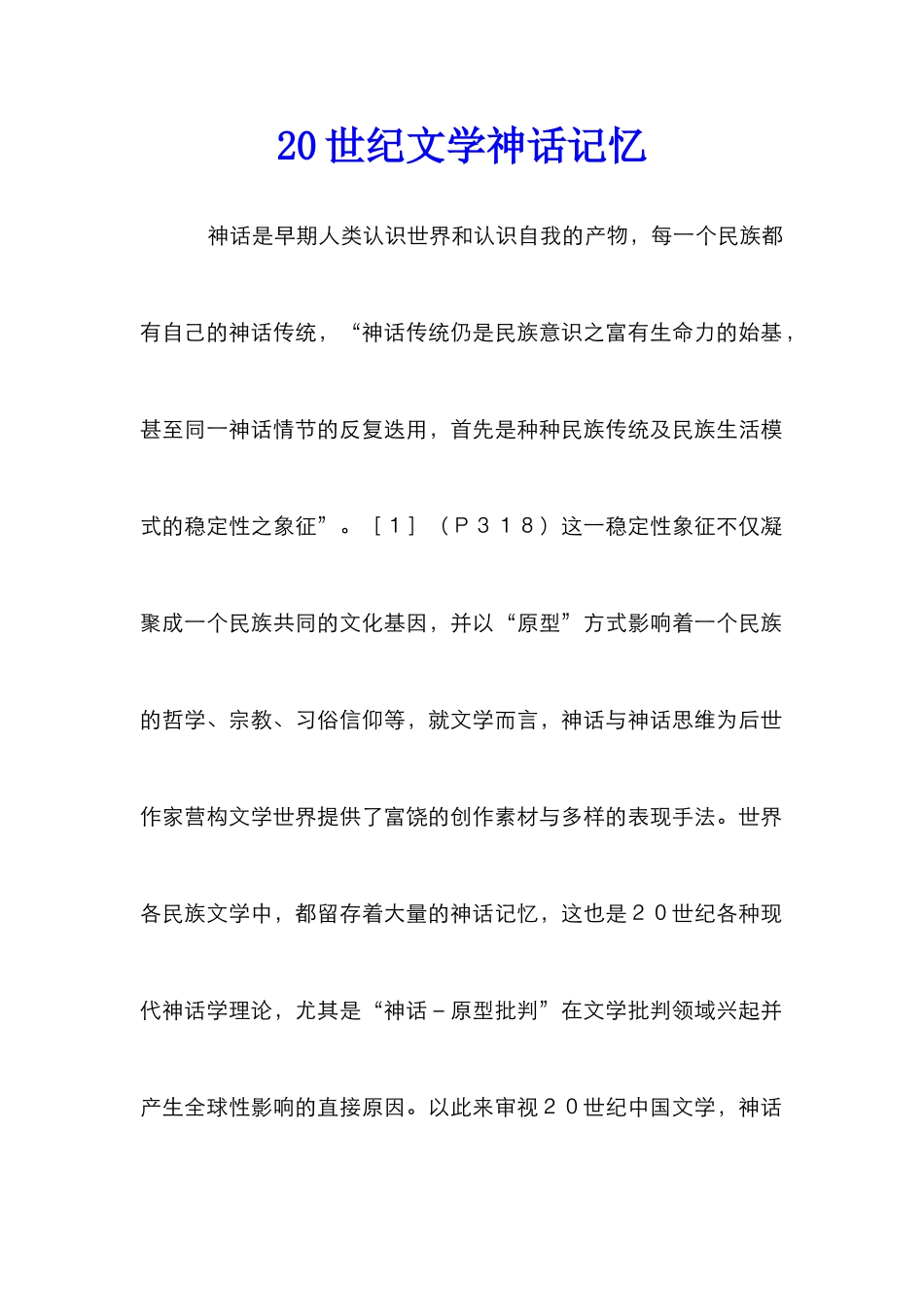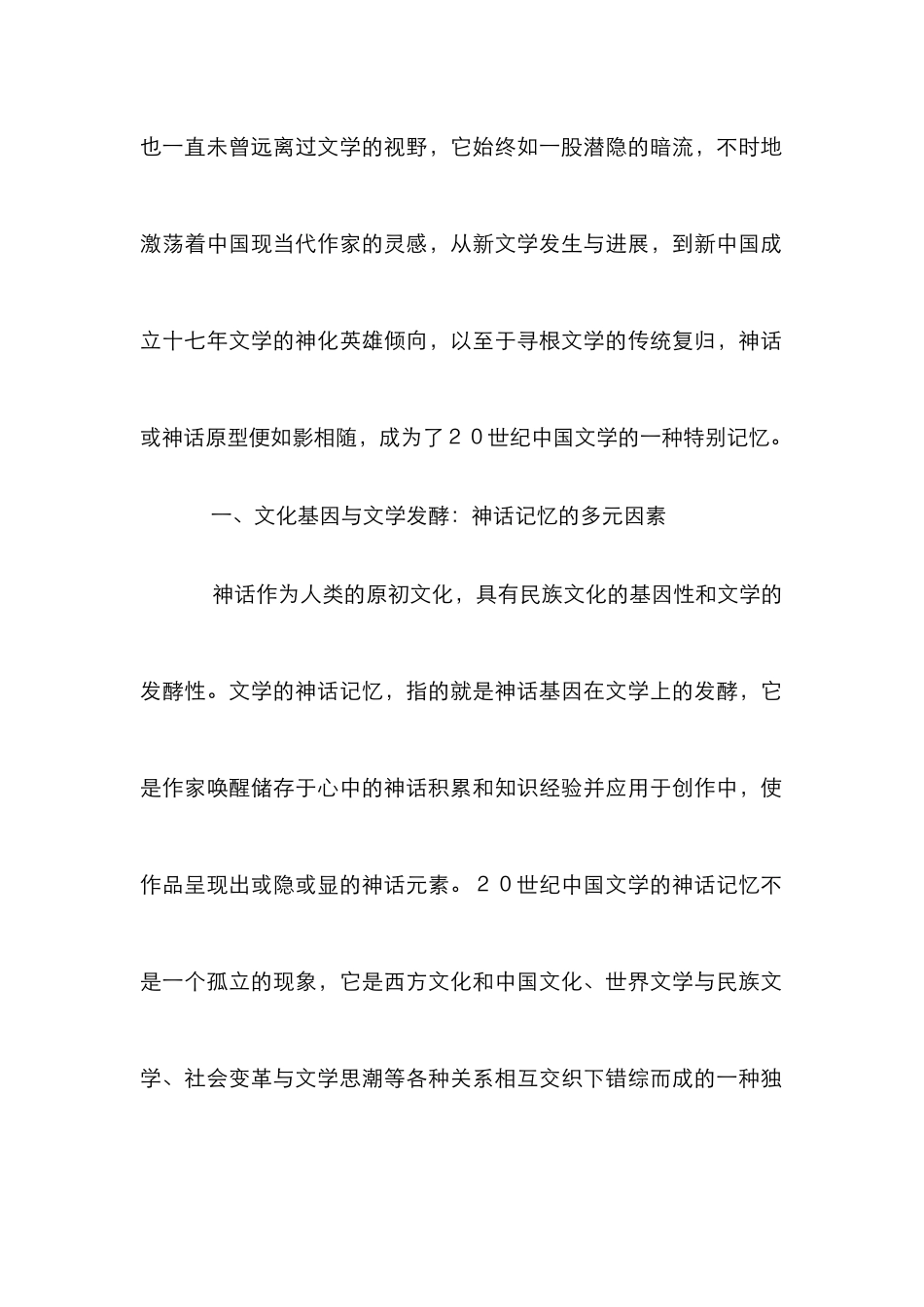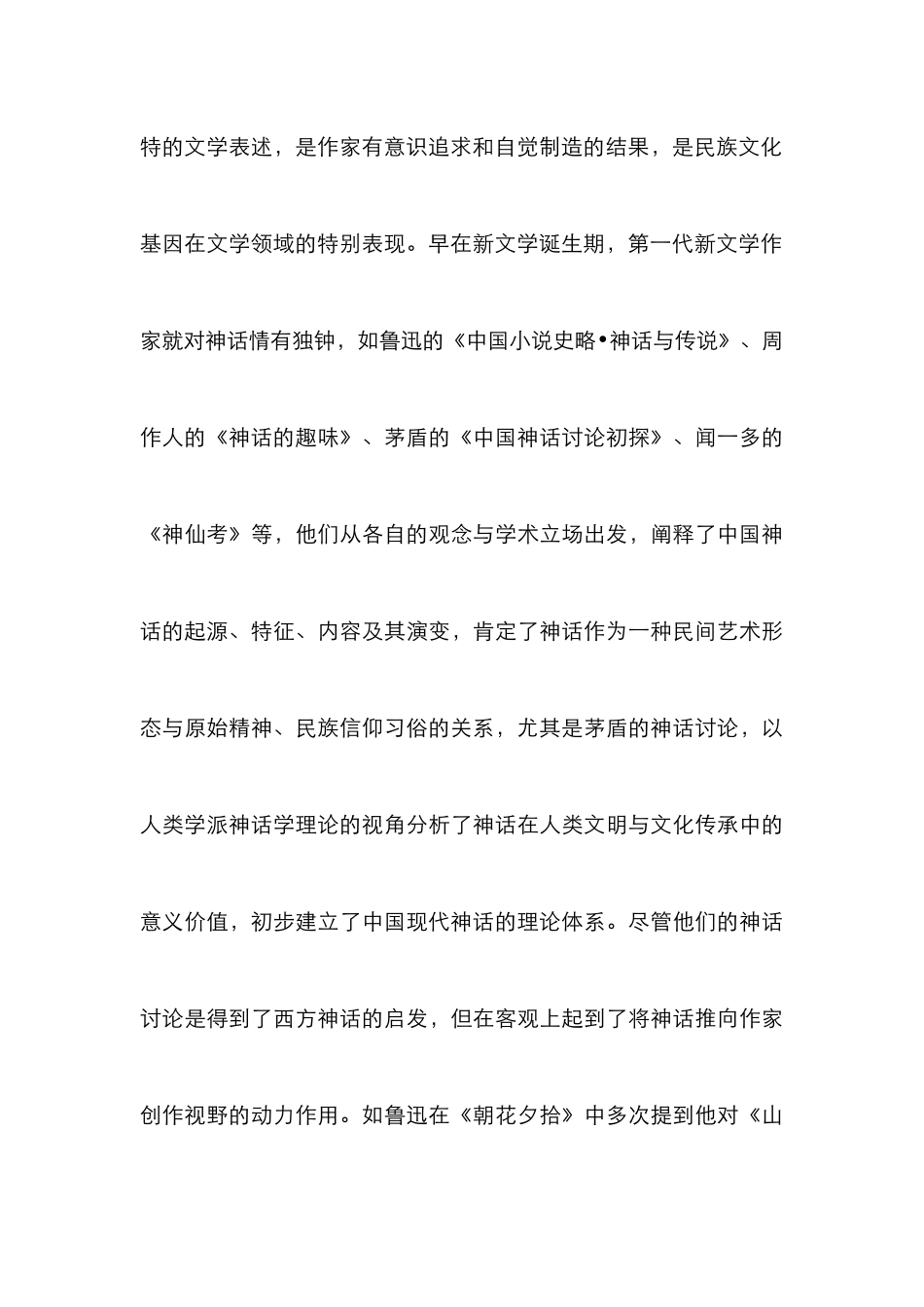20 世纪文学神话记忆 神话是早期人类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的产物,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传统,“神话传统仍是民族意识之富有生命力的始基,甚至同一神话情节的反复迭用,首先是种种民族传统及民族生活模式的稳定性之象征”。[1](P318)这一稳定性象征不仅凝聚成一个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因,并以“原型”方式影响着一个民族的哲学、宗教、习俗信仰等,就文学而言,神话与神话思维为后世作家营构文学世界提供了富饶的创作素材与多样的表现手法。世界各民族文学中,都留存着大量的神话记忆,这也是20世纪各种现代神话学理论,尤其是“神话-原型批判”在文学批判领域兴起并产生全球性影响的直接原因。以此来审视20世纪中国文学,神话也一直未曾远离过文学的视野,它始终如一股潜隐的暗流,不时地激荡着中国现当代作家的灵感,从新文学发生与进展,到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文学的神化英雄倾向,以至于寻根文学的传统复归,神话或神话原型便如影相随,成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特别记忆。 一、文化基因与文学发酵:神话记忆的多元因素 神话作为人类的原初文化,具有民族文化的基因性和文学的发酵性。文学的神话记忆,指的就是神话基因在文学上的发酵,它是作家唤醒储存于心中的神话积累和知识经验并应用于创作中,使作品呈现出或隐或显的神话元素。20世纪中国文学的神话记忆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是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社会变革与文学思潮等各种关系相互交织下错综而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学表述,是作家有意识追求和自觉制造的结果,是民族文化基因在文学领域的特别表现。早在新文学诞生期,第一代新文学作家就对神话情有独钟,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神话与传说》、周作人的《神话的趣味》、茅盾的《中国神话讨论初探》、闻一多的《神仙考》等,他们从各自的观念与学术立场出发,阐释了中国神话的起源、特征、内容及其演变,肯定了神话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形态与原始精神、民族信仰习俗的关系,尤其是茅盾的神话讨论,以人类学派神话学理论的视角分析了神话在人类文明与文化传承中的意义价值,初步建立了中国现代神话的理论体系。尽管他们的神话讨论是得到了西方神话的启发,但在客观上起到了将神话推向作家创作视野的动力作用。如鲁迅在《朝花夕拾》中多次提到他对《山海经》中神话形象的喜好,并认为“真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作品”即“无名氏文学”“比起希腊的伊索、俄国的梭罗古勃的寓言来,这是毫无逊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