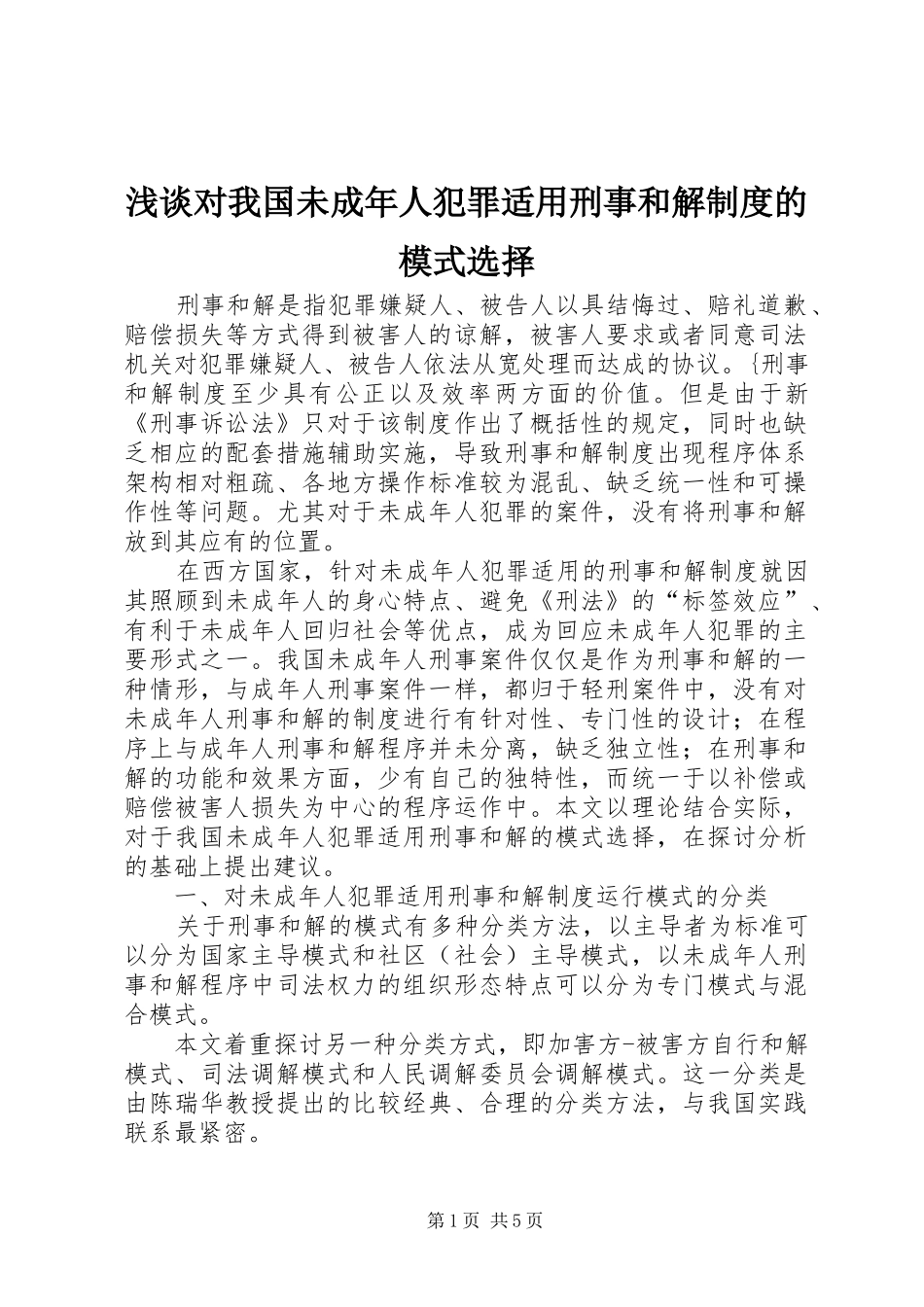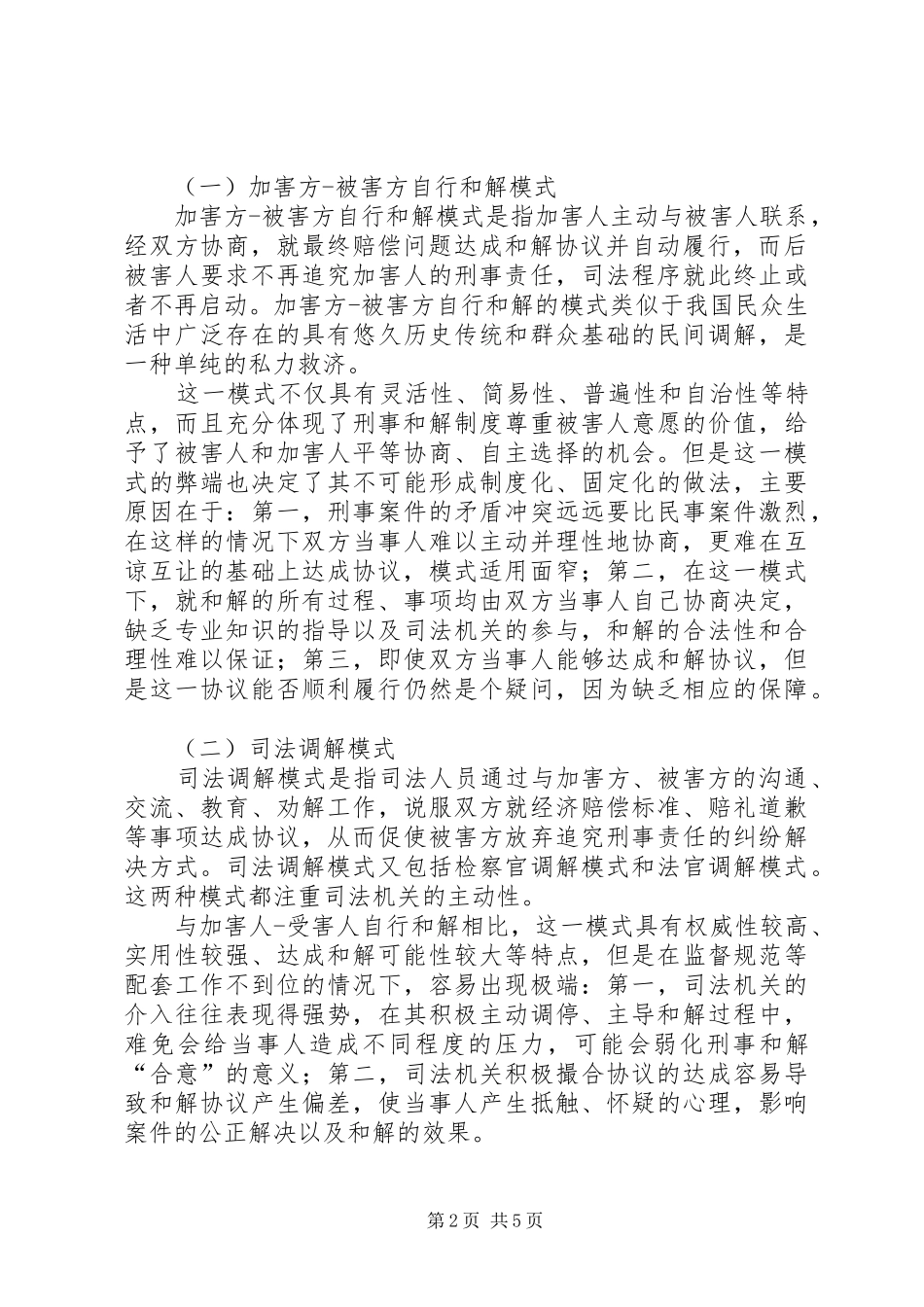浅谈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模式选择刑事和解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得到被害人的谅解,被害人要求或者同意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理而达成的协议。{刑事和解制度至少具有公正以及效率两方面的价值。但是由于新《刑事诉讼法》只对于该制度作出了概括性的规定,同时也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辅助实施,导致刑事和解制度出现程序体系架构相对粗疏、各地方操作标准较为混乱、缺乏统一性和可操作性等问题。尤其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没有将刑事和解放到其应有的位置。在西方国家,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的刑事和解制度就因其照顾到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避免《刑法》的“标签效应”、有利于未成年人回归社会等优点,成为回应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形式之一。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仅仅是作为刑事和解的一种情形,与成年人刑事案件一样,都归于轻刑案件中,没有对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制度进行有针对性、专门性的设计;在程序上与成年人刑事和解程序并未分离,缺乏独立性;在刑事和解的功能和效果方面,少有自己的独特性,而统一于以补偿或赔偿被害人损失为中心的程序运作中。本文以理论结合实际,对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的模式选择,在探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建议。一、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制度运行模式的分类关于刑事和解的模式有多种分类方法,以主导者为标准可以分为国家主导模式和社区(社会)主导模式,以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程序中司法权力的组织形态特点可以分为专门模式与混合模式。本文着重探讨另一种分类方式,即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模式、司法调解模式和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这一分类是由陈瑞华教授提出的比较经典、合理的分类方法,与我国实践联系最紧密。第1页共5页(一)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模式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模式是指加害人主动与被害人联系,经双方协商,就最终赔偿问题达成和解协议并自动履行,而后被害人要求不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司法程序就此终止或者不再启动。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的模式类似于我国民众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群众基础的民间调解,是一种单纯的私力救济。这一模式不仅具有灵活性、简易性、普遍性和自治性等特点,而且充分体现了刑事和解制度尊重被害人意愿的价值,给予了被害人和加害人平等协商、自主选择的机会。但是这一模式的弊端也决定了其不可能形成制度化、固定化的做法,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刑事案件的矛盾冲突远远要比民事案件激烈,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难以主动并理性地协商,更难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达成协议,模式适用面窄;第二,在这一模式下,就和解的所有过程、事项均由双方当事人自己协商决定,缺乏专业知识的指导以及司法机关的参与,和解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难以保证;第三,即使双方当事人能够达成和解协议,但是这一协议能否顺利履行仍然是个疑问,因为缺乏相应的保障。(二)司法调解模式司法调解模式是指司法人员通过与加害方、被害方的沟通、交流、教育、劝解工作,说服双方就经济赔偿标准、赔礼道歉等事项达成协议,从而促使被害方放弃追究刑事责任的纠纷解决方式。司法调解模式又包括检察官调解模式和法官调解模式。这两种模式都注重司法机关的主动性。与加害人-受害人自行和解相比,这一模式具有权威性较高、实用性较强、达成和解可能性较大等特点,但是在监督规范等配套工作不到位的情况下,容易出现极端:第一,司法机关的介入往往表现得强势,在其积极主动调停、主导和解过程中,难免会给当事人造成不同程度的压力,可能会弱化刑事和解“合意”的意义;第二,司法机关积极撮合协议的达成容易导致和解协议产生偏差,使当事人产生抵触、怀疑的心理,影响案件的公正解决以及和解的效果。第2页共5页(三)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是指公检法机关对于那些加害方与被害方具有和解意愿的轻伤害案件,委托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对于经过调解达成协议的案件,可不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这种和解模式的结构性特征是调解权与司法权的分离,调解委员会成为司法机关解决刑事纠纷的辅...